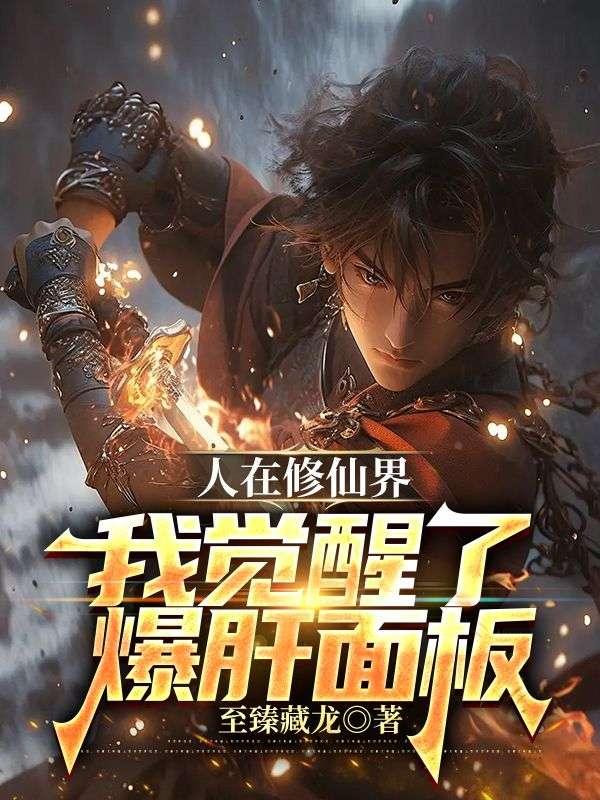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画舫无风月 > 第 19 章(第1页)
第 19 章(第1页)
顾喟撑着伞到山塘河的河埠头时,正是河上早市的时光。
雨天天色晦暗些,河水里是密密麻麻的小涟漪,买卖鱼鲜、菜蔬都在船上,比集市上新鲜不少,不仅是沿河几十条画舫,连河埠头上也有人在呼唤乌篷船:“爷叔让我瞧瞧大头花鲢”“倷阿是有新鲜的虾子”……
顾喟已经熟门熟路直接到花月舫边,正欲踏上跳板,突然在旁边的乌篷船上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
依然是长比甲搭裤子的使女穿着,长辫子垂在腰间,阴沉沉天宇间,仿佛就那鹅黄色的小袄和她的粉色嘴唇是一抹亮色。
她不光在买鱼买虾,还在和乌篷船上的人说笑:“陈二哥,‘鱼我所欲也,螃蟹亦我所欲也’,而且要最新鲜的。”
乌篷船上的人声音年轻,带着笑意:“侧寒姑娘,我这里都是最新鲜的好货。你看这蟹,揸开腿足有一尺长,要剥蟹粉都可惜了,最宜清蒸,那可谓‘半壳含黄宜点酒,两螯斫雪劝加餐。’多来两只,我便宜一点。”
侧寒笑道:“噫,读书人做生意,既然转文转得好,何故还要为几个臭钱斤斤计较的?我就不计较,反正买菜钱又不从我例钱里出。”
那厢答话也很轻松愉快:“我读两本书,根底里不还是渔家儿郎?岂能忘本?今日爹爹有些染病,我当然先尽做生意养家糊口,再谈读书。喏,书我也带上了,空闲时看两眼。”
侧寒说:“年底就要童生院试了,过了这一关,陈二哥就有了‘生员’‘秀才’的身份了,若能补廪,更能贴补家用,陈爷叔也没那么辛苦了吧。”
“哪有那么容易!”这位“陈二哥”笑答,“还是先卖鱼虾卖螃蟹吧,这样至少今日我家六口老小能买米煮饭。”
“今日没有订的酒宴,是自家吃的。不过也多挑几只吧,花雕腌了做醉蟹,蒸熟剥了做蟹黄酱都好,可以放几天慢慢吃。”侧寒边说边蹲在船边在竹篓里挑挑拣拣。
陈二哥也过去帮着挑拣,开始只是拿螃蟹,渐渐就凑得有点近,还在她耳边说:“蟹好不好不靠嘴上说,我已经蒸熟了几只,你尝尝就知道了。”
侧寒一甩长辫子,不着痕迹拉开一点距离,说:“行啊。螃蟹我自己挑,你去把蒸蟹再热一热,我可不想吃了肚子疼。”
顾喟心里一阵说不来的不舒服,后槽牙锉了锉,等那陈二哥捧出一盆蒸蟹时准备讨好姑娘时,他才在乌篷船边大声说:“花家的侧寒姑娘,我特为来讨你一碗面吃。”
挑了一篮子鱼虾蟹的侧寒回头,好像有点惊讶,但很快答:“我们画舫又不是早茶铺子。”
顾喟道:“下碗面而已,又不用八道点心八道粥面,还拒客于千里么?花月舫这么待客的?”
身形一拐,径自上了花月舫跳板,留下一句:“我就在花厅等你的面。”
陈二哥端着盆子,见那天青色身影进了船上,才悄悄问:“这谁呀?熟客?”
侧寒叹口气说:“是啊,胡县丞带过来的巡按,就好一口吃的,真难伺候!”
“巡按,京里来的吗?”陈二哥又瞟过去一眼,“看着蛮年轻呢,就一路中试,都选了官了啊!”
“嗯,听说还是个探花郎。”
陈二哥更羡慕了:“要是他给我指点指点文章,会不会我更容易中试啊?”
侧寒说:“算了吧,他总一副阴阳怪气模样,讨厌得很呢。”
又看看那一大盆肥壮得肚脐都凸出的蒸螃蟹,心里不甘,又不能不离开给客人下面:“螃蟹以后再吃吧。鱼虾蟹算账——客人来吃面,我要不伺候,妈妈又该打我了。”
她结清账目,陈二哥用荷叶包了两只蒸螃蟹递过去,说:“你忙,这熟蟹就带回去吧,空闲时再蒸一蒸就能吃,别推辞了。”还加一句:“特为给你留的。”
侧寒却不过,拎着一篮子鱼虾蟹,拿着熟螃蟹,还扶着肩上斜撑着的伞,轻盈地往花月舫走,放下东西后忍不住摸了摸脸上的伤痕,似有些不相信那渔家小伙子隐隐的意味,自己自失地一笑,洗了手开始做面条。
端到花厅的是一碗盖浇面,苏式细面条上盖着鳝鱼丝和冬笋、花菇一道浓油赤酱炒出来的浇头。
侧寒说:“顾大人,请慢用。”
顾喟脸色不太好看,先问:“那螃蟹怎么不剥出来做蟹黄面?”
侧寒说:“若做蟹黄面,剥蟹很费功夫,怕顾大人肚子饿等不及。”
“我有什么等不及的?蟹已经蒸熟了是现成的,我就要吃蟹黄面。”
侧寒看他这副挑事儿的尊容,一把把鳝丝盖浇面夺回去放在托盘里:“晓得了,请顾大人耐心等蟹黄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