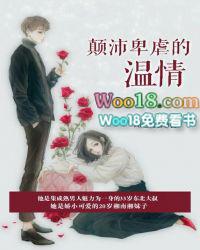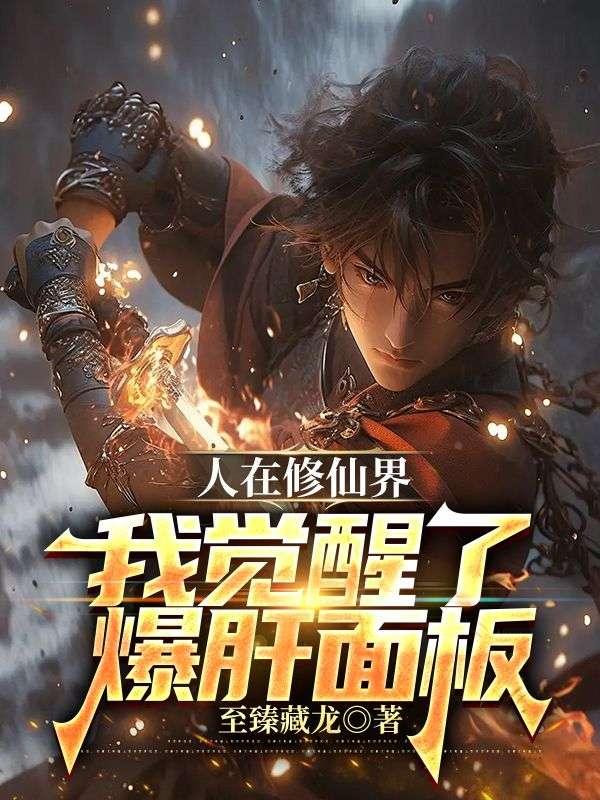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乱世如何开辟大航海 > 120130(第18页)
120130(第18页)
李氏已经在山东和京城附近开始安置生产造化
散的药厂了,毕竟造化散事关重大,除了身边的人,别人她也信不过。
虽然现在造化散还不可能供应全国,但是供应全军也够用了,等新的军医培养出来,新的药厂也建好了。
她看着低头看资料的众人,轻声道:“没有什么不可能,魏大夫有一点说的对,医术博大精深,或许很多人穷其一生也无法成为一代名医,但是世间疑难杂症虽多,更多的却还是风寒疮病,伤寒时疫,跌打损伤之类的常见病……”
“这些常见病自然有成品药,常见方,掌握了这些常见病的应对方式,自然也能为百姓尽一份力,世间万千百姓,如今能去的了医馆,开的起药的,十不存一,但是他们也是我们大魏的百姓!我作为朝中官员,以万民之税赋供养,自然要为百姓尽一份心!”
“不过既然是学堂教学,加不加入,自然是以自愿为主,并不强求。”
听到并不强制后,众人齐齐松了一口气。
宋时没有理会他们各异的神色,作为一群古人,尤其是面对自己吃饭的家伙变成教学,自然是有所抵触的。
俗话说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如果没有足够的保障,就直接让人家把自己的看家本事教出来,确实有些过分。
不过宋时也没有强迫他们的意思,他们可以自由选择。
也是现在刚抄了一波家,宋时手里刚好还富着,不介意在医疗上加大一点输出,先把框架搭起来。
没想到宋时刚说完,就有一个人站了出来:“在愿意加入医学堂和官家医院!大人所写《防疫四论》微言大义,又毫不藏私,以仁心妙术救百姓于水火,志向更是高远,此是苍生之幸也!如蒙不弃,在下俞嘉言虽然医术不精,也愿加入,若一身微薄医术能开枝散叶为百姓所用,也算求仁得仁。”
宋时抬头,却看到那人居然是在南京城中小有名气的俞嘉言,他医术精湛,为人一向脾气耿直,从不给人好脸色,因此得罪了不少人,年近四十了还只是守着一个小医馆。
但是也正是他,在药材不足的情况下,改良了三消饮、升降散和达原饮的配方,减少了贵重药材的消耗,让更多的百姓惶惶不安之际也能喝上一碗防疫的药汤。
宋时看着眼前的俞嘉言,心中欢喜,虽然他的名字有些小众,不如写出《本草纲目》的李时珍一般流名千古,但是宋时却恰好在后世听说过他的名字。
因为疫情的时候,她看过一个讲述古代防疫的科普,里面正好提到了俞嘉言。
另一条时间线中,俞嘉言原本是个儒生,屡试不中,后弃儒从医,在大魏灭亡后遁入空门,潜心学习医术,终得开宗立派,写下《医门法律》,设“六法八律“确立中医诊疗规范与伦理体系。
其中对于医案的规范已与后世无异,每治一病必详录医案,不仅包括望闻问切,同时记载天时、地理。除了病症本身的表现,也包括致病的原因,病情的发展变化,用药的记录,甚至药效作用的时间。
《医门法律》后成为代清太医署必修教材,甚至传至日本,促成汉方医学“古方派“革新。
其中俞嘉言对于疫病早有研究,不仅率先提出了“卫气营血“辨证雏形,还在《尚论篇》中明确区分伤寒与温病治疗差异。这在门户之见尤为严重的中医领域引起了轩然大波。
当然后来证明,俞嘉言说的就是对的。
别的不说,起码俞嘉言的人品和医术是经过了历史的考验的。
毕竟后世大魏灭亡后,不少的儒生为了不做代清之臣,纷纷弃儒从医,直接将医术这条赛道也卷上天,不过同时也将学阀之间的门第之见也一同带入了中医领域。
而在这样的风气与环境中,俞嘉言还能公开反驳当时医界滥用温补之弊,其勇气和心志可见一斑。
俞嘉言原本就对于疫病极有研究兴趣,在看到了宋时的《防疫四论》后,整个人的思路一下就打开了,颇有相见恨晚之感,更不用说防疫的全过程和疗效历历在目,再加上显微镜中那游走的微末小虫,更是由不得人不服。
等到看完宋时所写的医学堂规划报告后,只感觉一股热血涌上心头,恨不得立刻就让其中所写现于世间。
他虽然弃儒从医,但是原本儒家所学的兼济天下依旧留存于心,宋时的报告让他看到了另一条堂堂大道。
“如果宋大人真的要在全国的各县设立医学堂,福泽万民,在下愿意捐出自身经营的医馆!为百姓奉献绵薄之力,还请宋大人不要推辞!”俞嘉言一脸诚恳,一字一顿,然后深深的对着宋时鞠了一躬。
完全没有顾及旁边几个开医馆同僚的黑脸。
宋时的行为可是在公然宣称要抢医馆的饭碗,一旦官家的医院落地,就算不说那造化散贵的吓人的价格,就其他药材的成本价格,谁还会来他们的医馆看病?
这可是断了他们医馆的根。
但是有了俞嘉言带头,其他犹豫的人也纷纷响应,虽然未曾过半,但是宋时已经很满意了。
她所定的医馆和医学制度,延用了县学的部分制度,虽然现在还不够完善,但是框架却是和吏员考核升迁一个路子。
医学系统的搭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要开了头,其他的都好说。
光是宋时目前所提出来的构想已经让在场的所有大夫酥麻一片,仿佛看到了一片乌云倾盖而下。
有人惊惧交加,仿佛看到了医馆的末日。
但是也有人目放精光,看到一条除了科举以外的通天大途。
而且宋时保证,只要加入医学院,虽然需要将自己的毕生所学教给别人,但同时,整个太医院的医书,包括万物工坊研究出来的新药,都能提供给大家研究使用。
见识过造化散出神入化威力的众人哪里按耐的住内心的激动,堂中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