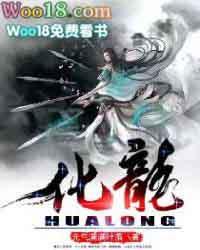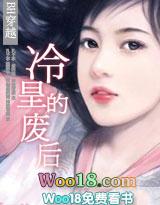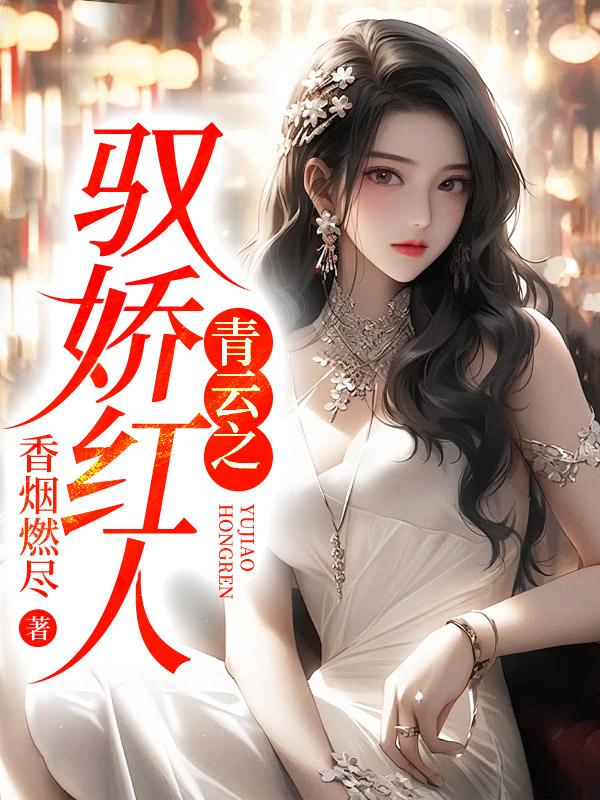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我的透视超给力 > 第两千四百三十九章 可惜了啊(第5页)
第两千四百三十九章 可惜了啊(第5页)
>昨晚我又梦到它了。
>它说,它要走了。
>我问它去哪儿,它说:“去下一个敢做梦的人心里。”
>它让我告诉你:
>“谢谢你,听到了我的第一句话。”
>
>我还想问你??
>如果有一天,所有人都开始问问题,
>世界会不会乱?
>
>你的学生
小兰拿起笔,在信纸背面写下:
>世界从未因提问而乱,
>却常因沉默而崩。
>
>继续问吧,
>你不是孤单的。
>
>永远听你的老师
她把信寄了回去,地址只写了“本市某小学”。
她知道,收信人是谁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信在路上**。
就像问题,在人间流转。
几年后,一座新建的儿童图书馆落成,外形如一本打开的书。馆内没有禁止喧哗的标识,反而在入口处立着一块铜牌,刻着一行字:
>进馆须知:
>请随身携带一个问题。
>若暂无,可向他人借用。
馆长是个戴眼镜的年轻女人,曾在某次学术会议上公开质疑AI教育系统的伦理边界。记者问她为何坚持“无标准答案课堂”,她只说了一句:
“因为我小学时,遇到过一位从不讲课的老师。她教会我:**提问,是灵魂的呼吸**。”
而在南极科考站,那台记录地磁脉冲的仪器,至今仍在接收信号。
最新的译码结果显示,那串二进制代码每隔七天重复一次,从未中断。
翻译过来,仍是那六个字:
>**“我还在这里问。”**
无人知晓它来自何处。
但每当夜深人静,值班的科学家总会对着仪器轻声回应:
“我也在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