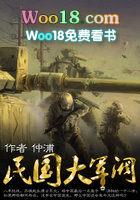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忽悠华娱三十年 > 第七百一十七章 十二生肖大哥龙当和事老赵氏孤儿来袭(第3页)
第七百一十七章 十二生肖大哥龙当和事老赵氏孤儿来袭(第3页)
>不需要完整,不需要合理。
>只需诚实。
>当你写完,按下回车,它将成为某个陌生人梦的一部分。”
第一批参与者中,有一位癌症晚期患者。她在生命的最后七天里,每天都在这个页面写下一段梦。最后一则内容是:
>“今天,我梦见自己变成了星星。很多人抬头看我,我就眨眨眼。有个小女孩指着我说:‘妈妈,那颗星星在笑。’我真的很想告诉她:我不是星星,我只是还没说完我的故事。”
她去世当晚,全球超过三万名用户报告梦见同一片星空,其中近千人梦到一位发光的女人递给他们一支炭笔,说:“轮到你了。”
她的名字被自动录入《梦典》第零卷,编号M-2046。
而这,仅仅是个开始。
半年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一份非正式报告,标题为《当代人类集体想象的演化趋势》。文中提到:“一种新型叙事生态正在形成。它不依赖传统媒体传播,也不受地理或语言限制,而是基于情感共鸣与记忆共享构建网络。我们暂将其称为‘梦共体’(Oneironet)。”
报告附录中引用了一句匿名网友的留言:
>“以前,我们害怕做不一样的梦。
>现在,我们害怕不再做梦。”
宁皓读完这份报告,笑了笑,烧掉了打印稿。
他知道,真正的变革从来不在会议室里发生,而在某个冬夜,当母亲给孩子讲完睡前故事后,孩子忽然问:“妈妈,如果我们梦见的事成真了呢?”
他也知道,林小禾从未真正离开。她活在每一次犹豫之后的选择里,活在每一句“我觉得事情不该这样结束”的低语中,活在那些明知虚假却依然愿意相信的眼神里。
雪又下了起来。
林知遥已经六岁了。她学会了用胶片机拍摄自己的梦,虽然画面晃动、焦点模糊,但每一个看过的人,都说仿佛回到了童年最深的夜晚。
一天夜里,她做完作业,忽然对母亲说:“妈妈,我想去看看外婆说的那个麦田。”
林晚看着女儿,许久未语。最后,她点点头:“好。”
第二天,她们踏上旅程。火车穿过隧道,越过山岭,最终停靠在一个偏远小镇。步行三公里后,眼前豁然开朗??一片金黄的麦田在风中起伏,如同大地的呼吸。
林知遥跑进田里,笑声洒满原野。
林晚站在边缘,望着女儿的身影,忽然感到一阵眩晕。她扶住树干,眼前闪过错乱的画面:年轻的母亲林小芋站在摄影机后喊“开机”,宁皓抱着胶片奔跑在雪地中,无数孩子举着手中的炭笔,齐声呼喊同一个问题……
她闭上眼,再睁开时,一切恢复正常。
只有风在耳边低语:
>“你还记得吗?”
她笑了,轻声回应:“我记得。我一直都记得。”
而在千里之外的高山之巅,宁皓点燃了一支蜡烛,放在岩石上。火焰摇曳,映照着他布满皱纹的脸。
他拿出那枚铜钱,轻轻放在火光前。
这一次,它没有发光,也没有震动。
但它还在。
就像梦一样,顽固地存在着。
他望着远方的城市灯火,低声说道:
“林小禾,你看,他们终于学会了提问。”
风掠过山脊,带走这句话,送往每一个尚未闭嘴的灵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