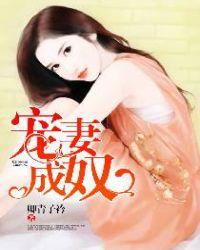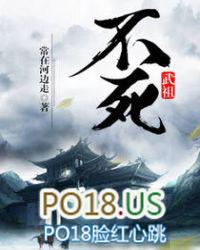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第一天骄 > 第六百六十三章 我即天命(第2页)
第六百六十三章 我即天命(第2页)
当时他不信。
现在他懂了。
他走出门,沿着山坡缓步而行,脚印在泥地上留下浅痕,很快又被新落的花瓣覆盖。山腰处有一片废弃的数据碑林,曾是旧时代纪念阵亡者的地方,如今已被藤蔓缠绕,铭文模糊。他曾提议拆除,却被市民议会否决。理由是:“它们提醒我们,曾经有过不愿放下的年代。”
他在一块倾倒的碑前停下。碑面裂开,露出内部嵌藏的微型存储器,早已锈蚀。可当他伸手触碰,竟有一丝微弱电流窜上指尖,随即,一段音频自动播放:
>“编号0,陈婉仪,死因:脑溢血。
>遗愿:请将我与丈夫共同经历的三十年记忆上传至公共缅怀网,供所有人调阅。
>特别备注:若儿子未来选择删除此记录,请尊重他的决定。”
声音戛然而止。
阿野蹲下身,用袖口擦去碑角的青苔,低声说:“你儿子去年已经删了那段记忆。但他每周都会来这里坐一会儿,带一束野菊。”
风吹过,树叶沙沙作响,像是回应。
他知道,真正的纪念,从来不在数据里,而在行动中。删除不等于否认,正如沉默不等于遗忘。
回到图书馆时,天色已近黄昏。门外站着一个少年,背着旧书包,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申请表??共忆之城青年志愿者登记表。他叫陆明,父亲三年前因意外去世,母亲至今仍每天重播他生前的最后一通电话录音。
“我想报名参与‘静默陪伴计划’。”少年声音发紧,“听说……可以帮别人学会放下。”
阿野接过表格,看到“动机”一栏写着:“我不想让妈妈再哭了。”
他点点头,没多问,只递过一杯热茶。“先坐下。”他说,“我们不急着开始。”
少年颤抖着手接过杯子,目光落在墙上一幅手绘地图上??那是全球十三个“释怀点”的分布图,包括这里的纸屋图书馆、旧东京废墟剧场、南荒祭司谷、北极光观测站……每一个地点,都曾发生过大规模集体释放记忆的仪式。
“你觉得,”阿野忽然问,“你爸最希望看到什么?”
少年愣住。
“是他活着时的样子,还是你现在这样拼命压抑自己的痛苦?”阿野轻声说,“如果你爸真的爱你,他会宁愿你笑,哪怕忘了他说过的某句话。”
少年的眼泪终于落下,砸在茶杯边缘,漾开一圈涟漪。
那一晚,阿野教他吹陶笛。音符断续,不成曲调,却有一种原始的真诚。当最后一个音消散在夜风中,少年忽然笑了:“原来……不完美也没关系。”
“当然。”阿野望着星空,“完美才最难放下。而真实,从来都有裂痕。”
几天后,少年的母亲主动联系市政厅,申请永久封存那段通话录音。她在提交说明中写道:“我终于明白,爱一个人,不是把他锁在昨天,而是让他活在我的今天。”
消息传来时,阿野正在整理一批旧书。其中一本《失语症诊疗手册》夹着一页泛黄的信纸,上面是裴无咎的笔迹:
>“语言的本质,不是传递信息,而是建立连接。
>当我们失去说话的能力,往往是因为害怕说出真相。
>而真正的沟通,始于愿意承受沉默的勇气。
>所以,不要怕说不出,也不要怕听不见。
>只要你还愿意坐在对方面前,哪怕一句话不说??
>那就是最深的语言。”
阿野将信纸小心收好,放进木盒,与苏清雪的留言并列。他知道,这些遗物不会消失,因为它们承载的不是过去,而是通往未来的桥梁。
春天渐深,忆春花园进入盛花期。市政厅宣布举办第三届“清明合奏会”,主题定为《带着遗忘启航》。不同于往年万人合唱的形式,今年改为“一人一音”仪式:每位参与者只需录制一段自己哼唱的《风吹过山岗》,无论音准如何,都将被合成一首宏大的交响。
阿野受邀担任开场引导者。那天清晨,他独自登上释怀亭,手中握着那只青铜指环。阳光透过云层洒下,指环表面浮现出细微纹路,竟是一幅星图??正是当年第六部构建星外孤岛时使用的坐标网络。
他举起手指,对着朝阳。
刹那间,光芒折射成七彩光晕,投射在空中,形成一座虚幻的桥,横跨城市上空。与此同时,全球十三个释怀点同时感应到能量波动,铜铃齐鸣,虽无物理连接,却奏出完全同步的音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