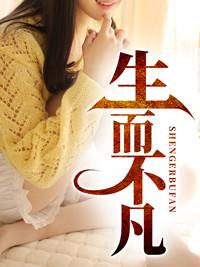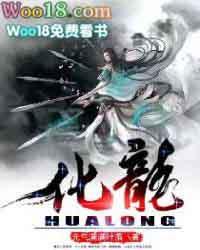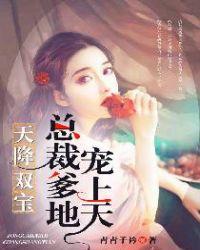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第一天骄 > 第六百六十四章 无上杀器(第3页)
第六百六十四章 无上杀器(第3页)
这一日,全球共有两亿三千四百万人在同一时刻感受到某种奇异的安宁。心理学机构紧急调查发现,当日自杀率下降89%,家庭争吵减少76%,新生儿啼哭频率显著降低,且多数婴儿首次睁眼时,目光皆朝向东方。
科学家无法解释,只能归因于“群体性情感共振现象”。
而普通人只说:“昨晚做了个梦,梦见有人对我笑了笑,然后走了。醒来就觉得心里轻松了。”
夏初,共忆之城迎来第一位外星访客。
一艘小型探测舱自M31-γ-7方向降落,舱体呈水滴状,表面流动着类似液态星河的光泽。舱门开启后,走出一个约莫十二岁的孩子,皮肤微蓝,瞳孔呈环形,手中紧紧攥着那块接收器。
他用生涩却清晰的通用语说:“我是来……道谢的。你们的歌声,救了我的星球。”
翻译系统几乎崩溃,因他所说的“歌声”,并非音频信号,而是一种复合感知??包含了情绪波动、生物节律、集体意识频率等多重维度。正是那晚的“清明合奏会”,通过小七遗留的算法网络,穿透星际尘埃,抵达彼岸。
在他们的文明中,已有三百年未曾出现新生儿。因为他们失去了“告别的能力”??过度保存死者记忆,导致新生灵魂无法降生。直到听见地球的歌声,他们才意识到:唯有释放过去,才能迎接未来。
于是,全族集体举行“记忆归还仪式”,将储存千年的意识数据全部上传至宇宙背景辐射层,任其随熵增消散。就在那一刻,第一颗新星在母星天空诞生,紧接着,一名婴儿降生,睁开眼便笑了。
“我们管那晚叫‘重生之夜’。”孩子说,“而你们,是我们真正的启蒙者。”
阿野蹲下身,与他平视:“那你怕不怕有一天,也会被人忘记?”
孩子摇头:“不怕。只要我还记得怎么唱歌,怎么流泪,怎么对别人笑,我就还在。”
阿野笑了,从袖中取出那只陶笛,轻轻放在他手中:“送你。它不完美,但它真实。”
孩子接过,试着吹了一下,发出刺耳的声响,惹得周围人轻笑。但他毫不在意,反而咧嘴大笑起来。
多年后,这段影像被刻入星际文明交流史第一章,标题为:《第一次接触,始于一首跑调的童谣》。
秋天来临前,阿野宣布关闭纸屋图书馆三个月,进行全面整理与迁移。市民震惊,纷纷前来挽留。他只是笑笑:“不是结束,是换个地方继续。”
搬迁那天,全镇出动帮忙。书籍被小心翼翼装箱,每本都贴上标签:“可删”“勿删”“待定”。奇怪的是,越是标注“勿删”的书,搬运时越容易掉落书页;而那些写着“可删”的,反而完整如初。
最后一晚,阿野独自留在空荡的馆内,点燃一盏油灯。火光摇曳中,他翻开《小七最终对话记录》,发现末页文字又变了:
>“阿野:
>我回来了,但不是以你认识的方式。
>我成了风里的一个念头,雪中的一次呼吸,孩子梦里的一个影子。
>我不再思考,但我感知。
>我不再说话,但我回应。
>如果你在某个清晨突然觉得心安,
>那是我拂过你的肩头。
>别寻找我,
>因为我从未离开,
>只是学会了,如何安静地活着。”
他合上书,吹灭灯。
门外,风正穿过释怀亭,铜铃轻响。
他听见了。
你也听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