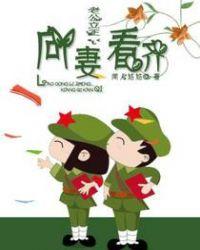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黎民日报 > 拉拢(第1页)
拉拢(第1页)
孟允抒坐在马车上,用炭笔在清单上的一家书坊名字后面打了个叉,而后以此为分界线,浏览着在这之上的部分。
当前她和盛催雪取得的成果在她的预估范围内,有多家书坊认为她的想法天马行空,或是由于种种限制不能放弃书肆的经营而婉拒了她们,但也有一部分书肆被她们争取过来,愿意尝试着将书铺完全改造成报亭或报社。
接着,孟允抒将视线挪向下一个目的地,那是个她十分熟悉的名字。
文昌书坊。
虽然她至今都不愿回想起她当时的劳动强度,但这到底是她创业的起点,难免会对它有几分怀念。而且,在胤朝,通常情况下同一行业的商人会将店铺聚集在同一条街道上,这样有利于招揽生意,也方便行会进行管理。
出于以上原因,孟允抒下定决心要将郭掌柜拉拢过来。
若是她能成功,等成立报业行会后,文昌书坊内的伙计和帮工也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
这个时段正是文昌书坊的客流高峰期,孟允抒跟着几名顾客一同跨进门槛,见郭掌柜正站在柜台后指挥伙计干活,便提高嗓门说了句:“郭掌柜,别来无恙。”
郭掌柜闻言转过头来,在看到孟允抒的一刻便满脸堆笑:“哎呀,孟社长,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
他向孟允抒行了一礼,但他的笑眼中却藏着几分揣度:“你我有些时日没见面了,不知你此番前来所为何事?”
“故地重游罢了,顺便见见老朋友。”孟允抒向他回过礼后,似是漫不经心地环顾着四周,扫了一眼店内顾客的数量,“郭掌柜果然是经营有方,文昌书坊的生意还是这般红火,与我离开时别无二致。”
“哎,社长真是抬举我了。”郭掌柜摆摆手,他听出孟允抒话里有话,于是吩咐伙计照看好书铺,对孟允抒说道:“既然孟社长是来找我叙旧的,那就请随我移步后院吧。”
后院是郭掌柜的私人住宅,不对外客开放,走入此处时,书坊内的喧嚷便被他们甩在身后。孟允抒经过庭院中的那几棵柿子树时,还见枝叶间落了许多麻雀,唧唧喳喳的叫声在空旷的院子中显得尤为响亮。此处环境静谧,倒是个谈话的好地方。
孟允抒进屋落了座,郭掌柜取来茶盏,一面为她倒茶一面笑吟吟地说道:“时至今日我都不敢相信,孟社长居然是女儿身。”他将茶杯放在孟允抒面前,自己也坐了下来,称赞孟允抒演技了得:“当初你在我这里帮工时,我可真是一点都没看出来。”
半年以前孟允抒通过小报澄清了陈府的凶宅疑云,不少人曾被这篇报道吸引而来,发现陈府摇身一变成为了黎民报社。文昌书坊离报社不远,郭掌柜自然一早就听说了此事。虽说报社与书坊不同,但两者也存在着竞争关系,于是他便跑去报社打探敌情,没成想竟然撞见了孟允抒,这才得知她的女子身份。
“身为探官,多少得有点乔装易容的手段,这些都不足挂齿。”孟允抒谦逊地笑笑,将话题从自己身上挪开,像是闲聊一般随口问道:“郭掌柜近来可好?文昌书坊的营收如何?”
郭掌柜却觉得孟允抒这话里有几分挑衅。
由于文昌书坊与黎民报社相隔不远,随着报社声名显赫,他首当其冲地受到影响。被抢走了那么一大批顾客,他的生意自然是每况愈下。而且这半年以来,他和孟允抒一直在暗中较劲,双方心里都和明镜似的,她显然是明知故问。
但郭掌柜到底是个经商多年的生意人,从不会将心底的不快表现在脸上,只是在话中暗藏机锋。
他笑容可掬地看着孟允抒说道:“托孟社长的福,在您的关照下,书坊的营收虽不如过去,但也勉强够糊口。”
孟允抒事先就已经掌握了文昌书坊的情报,她当然知晓书坊的生意大不如前。她这样试探郭掌柜,不过是为了让他亲口承认这一点。
现在她的目的已经达成,便不再和郭掌柜兜圈子,索性把话直接挑明。
“郭掌柜此言差矣,文昌书坊能有今天的局面,可不能把这笔账全部算在我头上。”孟允抒轻轻扬起唇角,声音却低了下去:“您心里应当明白,如玉行会也功不可没。”
通过此前的调查,孟允抒得知,如玉行会为了严格控制报业的规模,不单对黎民报社屡屡施压,还对那些售卖小报的书肆予以限制。革除这份副业之后,他们自然又要少一部分营收。
但与此同时,因为这半年的书业行情不景气,胡行长所获的利润大幅下跌,于是便将镰刀伸到了这些商户头上,假借各种会费的名号收敛钱财。
书商们对如玉行会积怨已久,却又畏惧胡行长的威势,敢怒不敢言。为了取得继续营业的资格,他们也只能服从如玉行会的条令,如数缴纳银两。
提到这事,郭掌柜更是苦闷不已,他无奈地摊手道:“那我们又能如何?若是退出行会,我们连开门的机会都没有,更何谈赚钱?就拿孟社长你自己来说,你不是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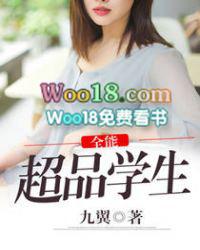
![[快穿]COS拯救世界 完结+番外](/img/7234.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