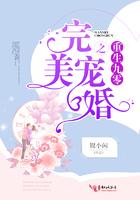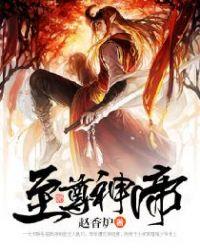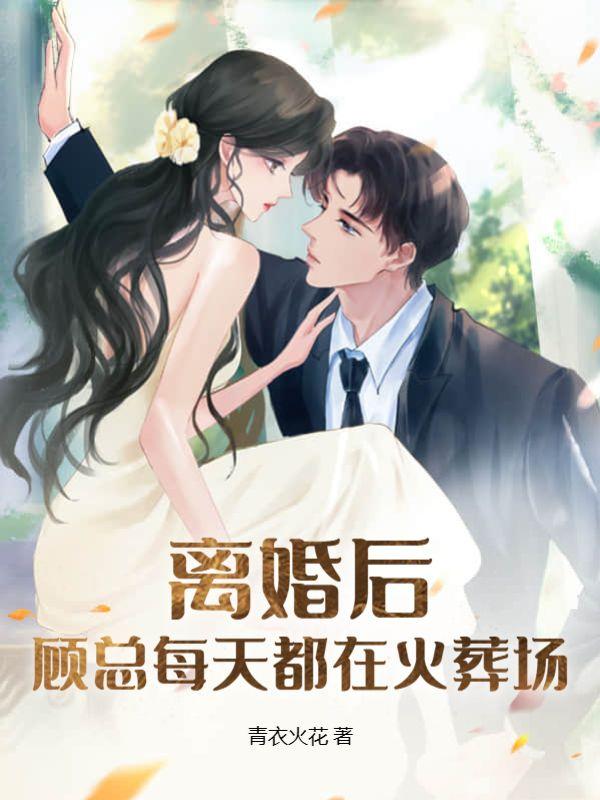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让你下山娶妻,不是让你震惊世界! > 第1547章 魔气湮灭(第1页)
第1547章 魔气湮灭(第1页)
“跳梁小丑,终于舍得露出尾巴了?”明川的声音冷冽如冰,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
他左手虚握,那凝固在空中的三道魔针瞬间寸寸碎裂,化为精纯魔气后被金色火焰彻底净化。
“啊??!”红袖神魂牵连受创,惨叫着踉跄后退,气息急剧萎靡。
“好个毒妇!竟敢对孩童下此毒手!留你不得!”金曼凤目含煞,周身紫色灵光暴涨。
化神期的威压如同实质,玉手抬起,便要施展雷霆手段将红袖当场格杀!
“哈哈哈……想杀我?!”红袖眼见败露。。。。。。
夜雨初歇,檐角滴水如珠,敲在青石板上,像谁在轻轻叩门。明川披衣起身,推开窗,山雾正缓缓退去,露出远处一片朦胧的蓝。忆璃花开得正好,花瓣沾着露水,在晨光中微微颤动,仿佛整座山谷都在呼吸。
他下楼时,阿萝已在药圃边等他。她手里捧着一本旧册子,封皮褪色,写着《归愿手记》三个字。“陆沉舟留下的。”她说,“他说这是老师最后几年的研究笔记,一直藏在国外图书馆的冷柜里,怕被查禁。”
明川接过,指尖抚过纸页边缘。那字迹熟悉而温润,是他母亲生前常写的那种细瘦行楷。翻开第一页,日期是1996年秋??正是她被捕前三个月。
>**1996年9月12日阴**
>今天去了城郊的孤儿院。孩子们眼神空洞,像被抽走了魂。他们不是不说话,而是没人愿意听。
>我给他们讲了个故事:有一群鸟被困在铁笼里,每天有人喂食,但从不打开门。后来一只小鸟开始啄铁条,别的鸟笑它:“你傻吗?这笼子结实得很。”
>它说:“我不是想逃,我是想让后来的鸟知道??这里本来不该有笼子。”
>有个孩子问我:“那你是不是那只鸟?”
>我笑了,没回答。可我知道,如果真有笼子,我就该去啄。哪怕牙齿崩断,也要留下一道划痕。
一页页翻下去,沈昭宁并非只写批判与控诉。更多时候,她在记录普通人如何在沉默中挣扎:一个教师偷偷复印禁书发给学生;一名医生为政治犯伪造病历延缓刑期;甚至有个清洁工,每天悄悄擦掉墙上“打倒XX”的标语,换上一句“天凉了,记得加衣”。
她的研究核心,竟与“归愿碑”惊人相似??不是为了复仇,而是为了让被抹除的人重新成为“人”。她称之为“记忆的微光计划”:通过口述、信件、日常物件的保存,构建一条不依赖官方叙事的记忆通道。
“原来……她早就想过这条路。”阿萝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
明川合上手记,走向后院的老槐树。那里埋着一节铜管,是当年从基地废墟带回的残骸,里面藏着一段未解码的记忆晶体。苏晚晴曾说它极不稳定,需特殊频率激活,否则可能引发强烈情绪共振。
他蹲下身,将手记放入新制的陶罐,一同封存。“等十年后再启。”他在纸上写道,“有些真相,必须等人心准备好才能听见。”
当天午后,邮差又来了一趟。
这次送来的是一张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他们在找你。”
照片上是一座废弃剧院,墙皮剥落,舞台中央摆着一台老式放映机。画面定格在一帧胶片上:一个年轻女子站在讲台上,手持话筒,神情坚毅。那是沈昭宁最后一次公开演讲的画面,二十年前被列为“一级违禁影像”,全球下架。
但在这张照片里,放映机旁站着几个人,穿着黑色风衣,胸前别着银色徽章??正是“新纪元共识会”的标志。
苏晚晴盯着照片看了许久,忽然起身调出卫星地图。“这不是国内任何已知地点……经纬度匹配的是滇西边境的一处废弃矿区。”她眉头紧锁,“他们在重播历史,用真实场景唤醒集体创伤。”
“目的呢?”阿萝问。
“制造殉道者。”明川写下,“让人相信,压迫从未结束,反抗必须升级。”
空气骤然凝重。
当晚,医蛊堂召开紧急会议。除了核心成员,还连线了三位海外学者??都是曾在联合国推动《记忆伦理公约》的参与者。视频中,一位德国心理学家沉声道:“我们监测到近两周‘创伤回流’网络流量激增三百倍。他们在用AI重建受害者临终场景,配上煽情配乐和断章取义的解说,传播速度远超事实澄清。”
“最可怕的是,这些内容打着‘铭记’旗号。”另一位南非专家补充,“人们以为自己在悼念,实则被植入仇恨模板。”
屋内无人言语。
良久,明川提笔写下:“我们不能阻止播放,但可以改写观看方式。”
众人不解。
他继续写:“让他们看真实的她??不只是演讲者,更是会疼、会怕、会为一朵花驻足的女人。”
第二天清晨,医蛊堂官网上线了一个名为《昭宁日记》的互动项目。没有宏大叙事,只有二十四段音频日记,由不同年龄、性别、方言的人朗读??包括那位曾撕毁作文的西北男孩。
每一段都来自沈昭宁手稿的真实片段:
>“今天吃了荠菜饺子,烫得直哈气。突然想起小时候外婆总说:‘苦日子熬过去,春天就有好吃的。’”
>
>“昨夜做了个梦,梦见自己变成一只蝴蝶,飞过刑场,落在孩子的课本上。醒来哭了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