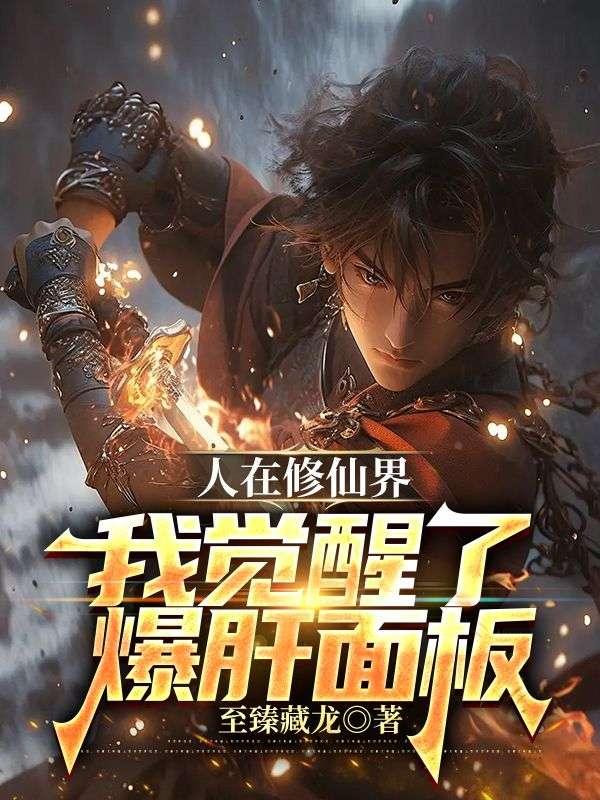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去白月光那当眼线 > 唱哪出戏(第3页)
唱哪出戏(第3页)
晏临的手虚虚抚上她的双手,将她托起。
“西厢房你还住的惯吗?一应摆设随你心意。”他浅浅地笑了一下,偏身过去拿出一根火镰,将桌旁的一盏油灯点亮。
灯火昏黄,并不足以照亮此刻夜色。但光影朦胧,温柔地勾勒出晏临姣好的面庞,尤其那一双含情眼,仿佛暖雾中浮动的春水,唇色在暖光映衬之下蒸得艳若衔朱。烛光顺着他略微开散的领口,缓缓流入腰封……
宋连慌忙将视线错开,咽下一口口水,抓住脑海里随便一件事就慌忙吐出口:“那群人?”
“我叫阿鲁去报官了,左右也没有伤亡,我想将此事压下。”晏临淡淡道。
宋连意料不得,顾不得立场脱口而出:“为何?”
“你是风宪台的人,我也想让你参与此事,”晏临正色道,“我怀疑,此事与先前许筠蘅交予我的案子有关。”
“啊?”宋连惊呼出口,随即赶忙收了声。
*
“恕属下多嘴,大人今日此举属实冒险了!”夜半三更,逍墨急匆匆回府,才敢进门就听公孙先生说了今日险况,又一想到昨日陈科的飞鸽传信,怎么也咂摸出些不寻常的意味来,怎能放心大人身边只有那居心不良的陈科!
“你看,我好端端的,”晏临宽慰道,“你不必忧心陈科,盯紧鸽子便成。”
“今日之事,可是那陈德生做的?”逍墨眼神向晏临全身扫了一圈,眼见无恙才稍稍安心。
晏临已沐浴更衣,发尾湿漉漉垂在肩头,一身白衣服帖地搭在身上,水珠滚滚流进领口,下午的血雨腥风仿佛从未发生,沉静地如同以往每一个展卷读书的夜晚。
“是,亦不是也,”晏临放下手中捧着的书,“许筠蘅交予我溪州一案,今日那刺客便操着溪州口音。”
“他们想阻挠大人查办?”逍墨急切道。
“非也,此事许筠蘅瞒得很紧,她并非粗糙冒失之人,若还能有人得知,必不是从这个渠道。”
“更遑论,还未查办,便来杀我这指挥使,倒像是把脖子递与我砍。”晏临慢慢讲解道,没有丝毫不耐。
“大人的意思是?”逍墨低头捉摸着,猛然间蹙起的眉毛舒展开,激动之余还不忘压着声音,“有人故意把大人目光引到溪州!”
晏临微露笑意,默默点头。“那人或许并不知晓我手中正握着这案子,但不论怎么说,他暗我明,顺着这条线慢慢摸索清楚便是了。”
“还有,陈科的事,不要与任何人讲。”
逍墨虽仍有疑虑,但他更信晏临,又嘱咐几句汤药别放凉便退下了。
汤药还烫着,屋里弥漫出一股子浓烈的苦涩味,晏临特意给西厢房周围摆了一圈气味芬芳的花朵,她应该闻不见。
他仿佛品不出这苦味一般,舀起来一勺,小口轻轻的吹散热气,缓慢送入嘴边,像在品鉴什么珍稀花露。
还有一点他未对其他人提及,他总觉得,那伙人的动机,不止于此。他们好像在试探他,特别是最后与那人缠斗之时,他几乎无法自控,身体使不出力气,可那人却也不急,一招一式,就与他慢慢磨着。
当年那场诡异的大病,他不是没有怀疑,时机太巧,动作又太迅速,昏迷之后再一睁眼,就在京外别院了。
祖父暴毙,正值公孙先生回乡探亲,棺椁匆匆下葬。而等到公孙先生回来,便是对他几番诊断,断不出下毒痕迹,恍如这病就是天然降临。公孙与祖父几十年的老交情,又是世代从医,晏临不会疑他。
但身体落疾有异,是如何走漏风声的?
巷口一战,背后观察着的眼睛,又是哪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