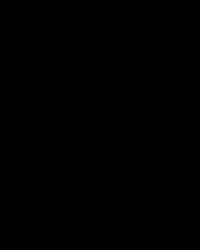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妻君薄情 > 7080(第16页)
7080(第16页)
花爹看到他扶人进屋赶紧阻拦:“你现在的身价怎能随意接客。”
“她可是我的救命恩人。”
他这条命都是她救回来的,身子给了又算什么。
雪公子用琴将花爹给径直推出去。随手将那木头扔到桌上赶紧小心翼翼扶着脚步虚浮的人在床上躺下。
姜漱玉进屋后闻到里面淡雅的清香味,神色清醒了些,面无表情地垂眸盯着人说:“干净吗?”
“大人我干净的,从未接过客。”
雪公子柔顺跪下,低下头让姜漱玉摸向他那圆润小巧的耳畔。姜漱玉只是想知道被褥是否换过,却被对方会错意。她抬手抚摸那处,少年闷哼一声,红着湿润的眼眸抬头看向她。
姜漱玉回想到,很久以前她也摸过一个人的耳垂。
她虽为太医但君后的身子一直由张老照料。那夜深更露重,她正好在太医署值守。有宫人来报说君后偶感风寒,让人前去请脉。
这事原本挨不到她,但天寒地冻又路面湿滑。张老年纪大了,行走不便就让自己前去。
那是她第一次近距离看到君后,从前只是远远望着那道浓重孤冷的墨色。近看才知道他生得很美,不是简单的皮肉之相而是骨子里的雅致风情。
明明是大虞最尊贵的男子可对后宫里的人都温柔有礼。但她总是能察觉到他眼底里的失意落寞。
那种虚无缥缈的感觉让她烦躁又安心,偶尔远远看见男人还会出神。
那夜她去请脉,明明做事素来谨慎,却不慎打翻汤药将他的雪白里衣弄湿。水滴顺着墨发往衣领里流去。
她慌张无措,刚要用衣袖擦干却不慎将那规整的里衣弄乱。手上是触手升温的软玉,男人闷哼一声,柔软的眸沁出水来。
他声音哑意中带着诱哄:“姜太医,你别这样。”
姜漱玉自认循规蹈矩,从未做过逾越之事。但看着那象征着处子之身的耳垂还是抬手摸了上去。
墨色翻涌,象征着守寡君后的外裳被人扯下。随后被轻薄雪衣所覆盖。两人都未经过事,她好歹同跃安亲近过。可檀礼连身子都未让人碰过,明明像是熟透的秋果却只是虚张声势的从容。
男人生涩地舔舐显得格外笨拙,她只能缓慢教他。两个在宫中孤单的人在冬日的风雪中相互汲取对方的暖意。
就如同这夜一般。
姜漱玉尤爱他发丝垂下的侧脸,有几分模样像檀礼。这夜她难得睡了好觉,所以连续几日都歇在风月楼中。雪公子得偿所愿,几日沉醉在服侍大人的喜悦中却浑然忘记了要事。
华灯初上,风月楼又热闹起来。花爹在门口徘徊很久,看人迟迟不出来,再听到里面难耐的喘息便只能硬着头皮下楼。
包厢内赵明若人逢喜事精神爽,一为升官,二为长子出嫁。她在太常寺多年,不少同僚为庆贺她当上寺卿特意在风月楼大摆筵席。
“不知长子许配给谁了?”
“是姜御医,对方也可怜本以为娶了一个陆家人,想不到是短命鬼。难怪一把年纪还没嫁出去,可怜姜大人新婚宴尔就又要独守空房啊。”
赵明若心知肚明姜漱玉娶的是君后,虽不知他用了何种手段出宫。但毕竟有悖世俗,或许这就是报应。
李信也过来凑热闹,举杯捧场:“赵大人今日要多喝几杯才行,我特意请了风月楼最出名的花郎给您捧场。他弹得一手好琴。虽然登不上大雅之堂,但听后让人畅快舒心。”
赵明若一愣:“可是那雪公子?”
“自然是他。”
赵明若曾听过他一曲,确实是妙音。
同僚听后赶忙起哄:“这雪公子怎么还不来?莫不是知道我们赵大人再不敢露面了。”
花爹知道这些人得罪不起,赶忙说道:“李大人,这雪公子今个摔了一脚,不如我换月公子给你弹曲儿。”
“知道我们今天宴请的是谁吗?这可是新任的太常寺卿,就算今日弹不了曲子,也要出来露脸罚酒啊。”
“这……”
“既然身体不适那就算了,”赵明若偏爱佳人,但也想听靡靡之音,“既然下不来我亲自上去听他弹奏一曲也行。”
花爹脸色煞白,眼看拦不住。但也想警告下雪公子,擅做主张接客简直是岂有此理。只能趁着人少说道:“赵大人实不相瞒,这雪公子在接客呢,对方是宫里的姜御医。”
赵明若听后面色铁青,白着脸直接一脚踹开那紧闭的大门。雪公子听见这动静吓得赶紧用被褥将自己身子遮住,但赵明若还是看到他身上缠绕的金线。那滴血般的玛瑙在人身前随着乌发晃荡,衬得肤色更白。
之前看雪公子清俊乖巧,想不到这床事上如此放荡。
姜漱玉看到来人,依旧淡定。先是将身后雪公子露出来的圆润肩头遮盖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