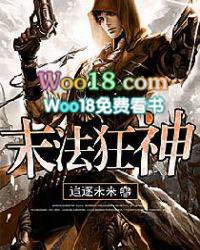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穿书给权臣冲喜后 > 200210(第7页)
200210(第7页)
吕绅在政事堂里仔细观察了两年多,终于不得不承认,当年他和潘济完全看走了眼。
姬安和上官钧从没有为权力争斗过,恰恰相反,他们在执政立场上一直都是一致的。
吕绅不知道在西祥接收京中消息的潘济能不能看透,但吕绅自己,现在可以说已经被半架空了。
若是按潘济所想,在即将开战之际,抓着一件小事做文章,无非就是仗着姬安要优先保障西北战事,为了稳住朝堂只得做出让步。
但,只有战事不顺,讨到的便宜才有可能占得住。如若战事顺利,等姬安抽了出手,必然会把这次搞事的人全都摁下去。
难道……潘济觉得这一仗会输?
吕绅不由得皱眉——潘济不会是想做点什么吧……
不过,他随即又微微摇头——应当还不至于,潘济年轻时也对西北有过野心,再怎么样也不会做出叛国之事。
那么,就是潘济很不看好这一仗。
其实这也是吕绅至今的困惑之处。
除非能一战攻下打骨鲁都城,把打骨鲁赶回草原上去流浪,否则,他真想不出有现在开战的必要性。即使他猜到有新武器,但战争不是光有武器就行,何况打打骨鲁的最困难之处反而不在前方,是在粮道。
还是说,姬安根本没想过进攻打骨鲁都城,就单纯地只是往西北推进,打下几座关隘城池?但仅仅是这样的目的,姬安会亲征吗?以吕绅的观察,姬安并不像是这样好大喜功的人,上官钧就更不是了。
吕绅改而按揉额侧——看不透,他完全看不透。
但他知道,姬安和上官钧都不是能容人挑衅的性子。
吕绅目光落在放于桌面的老花目镜上,那是丰泰二年他过寿时姬安赐的。近年来他看小字越发吃力,戴上这目镜就能好上许多。
姬安向来是个大方的天子,若是老老实实跟着姬安走,还能分到一口汤喝。哪怕今后家族利益有可能会受损,但至少自己这个小家可以保全。
吕绅叹口气,提笔给潘济回了封信。只夸了夸大理寺反应迅速,没有让骗局扩大影响天子声誉,别的都没说。
唤仆从进来将信送去驿馆之时,他顺便吩咐人去叫自己在京中的几个得意门生来家里吃饭。
总之,吕绅打定了主意——不管先前那批被打压的人想做什么,这回自己都不再掺和。
等这一仗打完,或许他就知道该如何选择了。
○●
元秀秀和郭签行骗的案子,消息压在帛兴县和大理寺内部,姬安没有对外公开。
丰泰四年的元月,姬安好好待在宫里,和亲信内侍们一同过元旦假和元宵假。内侍们则是仔细地帮他准备西行之物,每日凑一起商量检查,弄得姬安都有些哭笑不得。
原本姬安没打算带内侍。上官钧的四个小厮还多少会点拳脚功夫,可姬安的六个内侍就一点没练过,姬安担心他们跟去不安全。
但内侍们更担心他,磨着姬安求了一个假期。姬安经不住他们磨,最后只得答应带上何万利和汤开泰。何汤两人以前去过北边,西北边境也包括在内,算是熟悉一点气候和风土。
到了正月十八,元宵假结束。
姬安和上官钧商量好,会在这一日的早朝上公布御驾亲征一事。
不过,姬安没想到的是,还没等他给群臣一个惊吓,就先有臣子给了他一个惊吓。
众臣刚行过礼,一位翰林院大学士就迫不及待地出列:“陛下,臣有本奏。”
姬安寻个舒服的姿势倚着软枕,示意郑永回覆“准奏”。
汤大学士:“臣听闻,大理寺年前审理了一桩涉及陛下的大案,有离宫的宫女与宦官编造诞下龙子的谎言,在民间行骗。”
姬安不由得蹙下眉,转眼去看上官钧。
上官钧微微摇下头,示意自己没有接到消息。
大殿后方则是已经发出些许嘈杂声。
既然被提起,姬安也没有再瞒,回道:“确有此案,且已经审结。汤卿可是有异议?”
汤大学士续道:“不敢,大理寺断案迅速,令臣钦佩。只是,此事因离宫的宫女与宦官而起,还当防微杜渐。陛下仁慈,允宫女宦官每月出宫,听闻羽林卫还进入后宫值守巡逻。臣以为,此举不太妥当。”
他这话音一落,殿里的嘈杂声倒是很快停了。
不少官员原本还对那案子好奇,此时听到事涉内帷,已是心下打个突,连忙垂下目光,眼观鼻、鼻观心地站好。
姬安轻轻哼了下:“怎么,汤卿打听得这么清楚,是想管到朕的后宫去?”
汤大学士微微躬身,态度却是不卑不亢:“臣不敢。但,后宫之人方便外出,还有外男可出入后宫,通往前朝的门也不再上锁。这些都对陛下的安危极为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