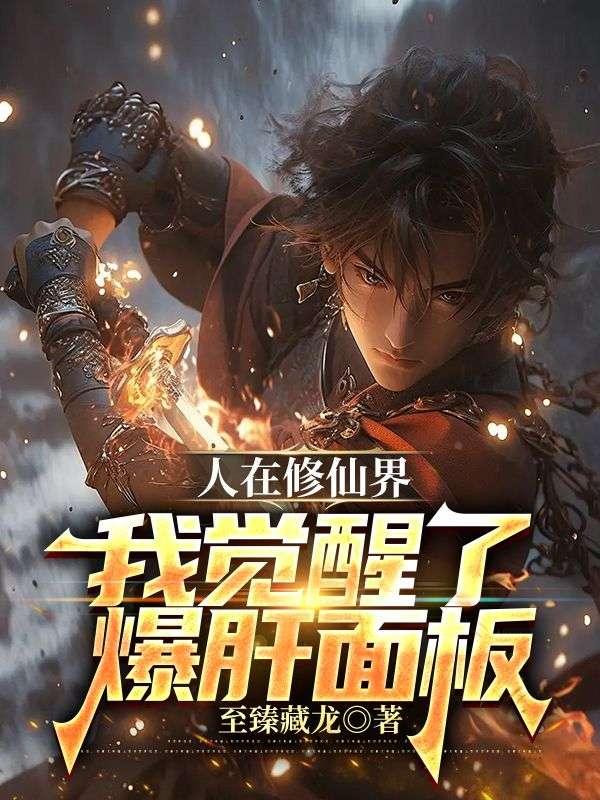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两京旧札 > 4050(第12页)
4050(第12页)
“宫牌……”张嬷嬷惊讶,“大姑娘您不进宫学画了?”
穆宜华抬眼,看着吴尚宫远去的背影:“不进宫了。”
大门外,吴尚宫仍旧是那副严肃的表情,她抬头望向站在前堂中央的穆宜华——都说大理寺狱走一遭,是个人都会皮脱骨无人样,头铁的服软,嘴犟的屈从,可穆宜华却好似从一颗温润的珠玉变成了硌手的砂石,看着仿佛是在人心里头长了根刺-
穆宜华的病一养就养到了十月中旬,日日在家中画画看书,无聊了便在芳园里头溜达几圈,出出汗气色倒也是好了。自从按时用药后,她便不再梦魇,等自己精神头好点,便差人去瞧了许掌柜,还命人送去名贵药材,包了所有郎中钱。
穆宜华有意地将自己与外界隔绝,相府嫡女卷入命案,即使是无辜遭殃,那也是整个汴京城里头的新鲜事儿,好要让他们嚼上一阵呢,此时避世是最明智的选择。
可她不出去,并不意味着外头的话传不到府里来。小丫鬟出去采买多少会听说一些,她们不敢闹到穆宜华面前,但也拦不住私底下与亲近之人说几句。穆宜华身体不适懒怠管,张嬷嬷却是一听见就掌嘴罚银钱,渐渐地后宅也就无人议论。
一日,穆长青气势汹汹地冲回府,茴郎在后头撑伞却也跟不上。穆宜华方在园子里赏雨品茶,看见穆长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连忙把他叫住:“你过来,脸怎么回事?”
穆长青不情不愿走过去,绷着脸不说话。
“茴郎,他不说你说。”
穆长青狠狠地瞪了一眼茴郎,茴郎刚想开口都被吓了回去。
穆宜华猜了七八分:“同别人打架了?”
茴郎瞥了一眼穆长青,小心翼翼点头。
“因为我?”
穆长青不说话。
穆宜华头疼扶额:“他们说什么了?”
穆长青咬牙仍旧沉默,可眼眶却红了。
穆宜华看向茴郎,茴郎也是一脸愤慨,哭丧着脸:“大姑娘,外头那些人的嘴巴就该缝起来!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却以为自己说什么都是对的!”
穆宜华沉默一瞬,仍旧问道:“说什么了?”
“有什么好讲的!”穆长青扯了一把茴郎,“给我拿衣服去啊,还杵在这儿干什么?”
茴郎唯唯诺诺,躬身离开。
穆长青越想越气,低声咒骂:“明明官家已经发了邸报,真相大白,他们还这么说你。一群不怕烂舌头的家伙!”
穆宜华垂下眼眸,神情淡漠无力:“好了,有什么好生气的。气坏了自己,外头那些人也不会闭嘴,倒不如耳不听心不烦,由他们去吧。”
“姐姐,难道就这么忍了!”
“那你还能怎么办?”穆宜华心烦,说话的语气有些重,“去脚店茶馆瓦肆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割了他们的舌头,堵了他们的嘴?别说是我了,爹爹当年被定为奸党赶出汴京,即使如今回来了做了副宰,也还有那么多白眼冷遇。就算是当年权倾朝野的刘太后也因为借子摄政之事为天下人诟病至今,我不过是汴京城中区区一个官宦闺眷,我能做什么?你想要我做什么?”
穆宜华说着说着,也有些气血上涌。
穆长青本只是为姐姐打抱不平,却反被姐姐骂,心中也不好受,还想争辩却被穆宜华瞪了回去:“最近不许出门,读完书就回来,哪儿也不许去。”
穆长青瘪瘪嘴,赶紧灰溜溜地离开。
穆宜华看着他离开,方才一直压抑着的酸涩突然涌上心头,眼泪刷的一下落了下来。
春儿连忙递上绢帕给她拭泪,心疼道:“大姑娘,小公子也只是为你抱不平。”
“我知道。”穆宜华抹去眼泪,红着眼道,“我刚刚是不是不该那么吼他?你说他这个年纪正是结交朋友的时候,自尊于他而言多重要,可就是因为我……你看看他今日被人打成什么样……”
春儿安慰:“奴婢一会让就给小公子送药去,而且我们小公子素来活络,不会吃亏,大姑娘不要担心了。”
穆宜华招手让她下去,只自己一人呆在园中。
一场秋雨一场寒,人心惆怅,所见皆是枯黄萧条。
穆宜华并不是不在意那些言论,那不过是在弟弟面前强撑姐姐面子的说辞罢了。众口铄金,三人成虎,人言可畏,她怎能不怕?
什么狐媚妖祸,不守妇道,四年前早背着骂名了,如今怕是还会加一句蛇蝎妇人。咬耳朵嚼舌根之人,若是让他们抓住了一丁点儿他们所谓的秘闻错处,哪怕是空穴来风,也相信众人呼吸山海倒,秉着义正言辞,说着满口胡话,为之针砭时弊、守节体国。
穆宜华也不是没尝过,只是如今身心俱疲,即使心中再不甘再厌烦,也唯有眼不见为净的法子。
“大姑娘,”春儿匆匆从前堂走来,手中捧着一摞书,上头还有一个盒子,欣喜道,“左大夫刚刚来送东西了。”
穆宜华微微一愣:“左衷忻?他人呢?”
“送完东西就走了,说是有要事要办,大姑娘出狱后没来问候您,今日便顺路送点东西,还说什么药材补品大姑娘您这儿肯定不少,他就送了些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