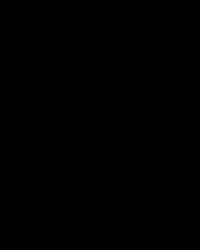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公主大人和娇娇暗卫 > 第 6 章(第2页)
第 6 章(第2页)
任平把目光锁向了公主身后的拔步床,那是个很好藏人的东西。他的左脚就要迈上木阶,明洛刺出了长剑。任平侧侧肩膀便避过了,明洛直接下起杀招,绝不肯让他迈进一步,但又被他轻松举刀挡住。刀剑碰出震耳的铮鸣声,他还是踩上了木阶。
然而这时,外面大乱起来,一声声的禀告如水浪般传开回响,把他的杀意遏止在了脚下。
“谨身殿走水,谨身殿走水了!请都督与厂督速速回宫救驾!”
“什么?!”
老太监慌张赶出去,任平回头看向厅外。明洛刺向他的心脏,他撇着刀退下木阶,顺带避过。所有人都看向了皇宫的方向,任平飞身站到重檐上,果真看到那片巍峨宫殿中,一只手掌般的火舌舔破了黑夜。
热闹退出公主府,向宫闱涌去了。这里又变得安静起来。
赵容璋拍拍明洛的肩膀,明洛的胸膛还在剧烈起伏,可见气得不轻。她让她领人把浴桶搬出去,换只新的,重新装满水。明洛吁出一口气,由衷道:“殿下真了解任平。”
火烧谨身殿是一早定下的计谋,是极好的调开所有人注意力、把驸马暴毙之案的重点转移到赵珏身上的法子。这场火他们将找不出任何具有纵火嫌疑的人,最后会被归因于皇帝失德不仁,触犯了天容。谁让赵珏没脑子,如此心急,都还吃着素,就要把她逼嫁。
别说是完全不知内情的百姓了,就是他们总挂嘴边的多少锦衣卫多少禁卫军,千方百计地去捉、去防那个左都督口中叫“玄猫”的杀手,却始终连个影子都追寻不到,驸马仍是一个接一个的死,也会怀疑是不是老天降罪于新帝,殃及了这些可怜的准驸马。
一日捉不到观玄,天下人就一日不能相信他们那个骄纵无知、被软禁将近三个月的公主能有什么反抗新帝的能力。
赵容璋让明洛取了几锭金子,赏给今夜来回搬水运水的宫婢。她们都走以后,赵容璋持灯往帐后走去。
这里黑漆漆的,烛火照出的光晕一点一点染亮了纱帐,也染亮了躲在这里纹丝不动的猫。猫握着护腕,直到微晃的火苗将他的脸整个照亮,他抬起了润亮的眼眸。
事发突然,猫身上的衣服没能穿齐,领口胸膛露了一片。光晕往下移去,猫很明白殿下的视线也跟着移去了那里。
他躲了躲脸。
殿下欣赏着他,含笑道:“过来。”
观玄垂眸走到公主面前。
赵容璋握了顶端,把玩两下,小哑巴呼吸骤乱,唇微张着,眼神湿漉漉的,不知道要放到哪里。他只能克制地站着,任凭她作弄。湿意渗透了衣料。
“这么久了,你要撑到什么时候?”
她下手越来越重,小哑巴脖子都红了,鼻腔里开始泄出一些哽塞的气音。
赵容璋想到方才种种,他就这么挺着躲在她的后面,怎么都消不下去,这副模样……
浪。她随口一说,恶劣地评价。小哑巴却十分痛苦,身子都有些颤抖了,脸上再次浮出被她压着含下时的红晕。他很需要支撑,却不敢轻动,更不敢靠到她的身上来,就这么低着头大口地喘气。本就一掌难握的挺翘却非但不能如他所期盼地恢复正常,还偏要坐实她的评价,兴奋地撑满她的手心。
赵容璋突然觉得这柄灯很多余,白白占用了她的一只手。他的反应太让人心痒了,让人想欺负个彻底。
有何不可呢。赵容璋吹灭手里的灯,随手丢掉,铜制的灯盘骨碌骨碌滚下木阶,这帐后的角落重新陷入了黑暗。观玄感觉到后腰伸来一条柔软的手臂,将他轻轻一环。高昂的挺翘,也未被放过。他就这样被揽抱着、抓握着,混乱中被公主的脚尖步步逼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