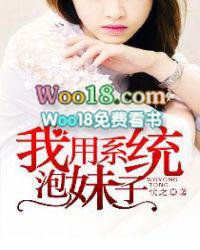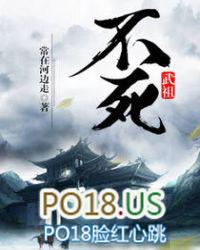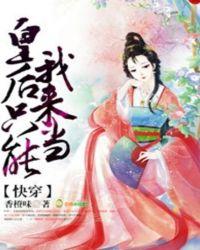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广夏:文德皇后 > 流年(第1页)
流年(第1页)
“我们困在时间回环往复的涡流里了……”这是长孙青璟在这三四年里经常生出的念头。她也经常站在终南山的松涛林泉间,发出和兄长及他的诸位好友们一样的质询:“开皇大业将会千秋万代,既寿永昌吗?”
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皇帝开始四处巡游只是一时兴起,新的宫殿新的运河会成为帝王起居注里一朵并不艳丽的插花;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洛阳那些白衣白袍自称弥勒佛降世闯进宫禁之中的人也无非是为了在这平淡的治世留下妄想的大名;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辽东的战事只此一次,灰头土脸的皇帝总会回到拥戴他的关中;一开始,所有人都认为那些死在运河工地的民夫与被强征入宫的少女与自己无关,总有人活该成为开皇大业的垫脚石——直到黎阳传来杨玄感反叛的消息。
叛乱发生在好大喜功的国朝二代皇帝第二次亲征高句丽期间,勋贵子弟们开始抱团叛乱,局面瞬时震悚和微妙起来。
大兴城一下子戒备森严,中原叛军与官兵作战的各种消息纷至沓来,谁也说不清关中的静水深流下潜藏着涌动的潮汐裹挟了多大的能量。
被家族抛弃的痛苦并没有维系多长时间。就连高士廉也惊异于两个孩子在历经阴谋与背叛后并未被噩梦环绕,从而成为性格乖张阴郁的可怜虫,然后用一生印证长孙安业最恶毒的妄语:“看,那个齐国疯女人的后代!”
恰恰相反,长孙无忌和长孙青璟野蛮执着的如同掉入山崖缝隙间的种子,在并不适宜的地方破土,盘虬卧龙般地去扎根,去寻找阳光,不顾一切地生长。
长孙炽曾经特意与高士廉商议接回弟弟这一双儿女的事宜。但是高士廉对妹妹所遭受不公的质疑,无忌对未来侃侃而谈,青璟云淡风轻地表示绝不离开九品官养父时,长孙炽知晓所有的挽回也都是徒劳。
不过长孙炽转而安慰自己:他们都是代北人,流淌在血管里的蛮横与狠戾会适时地冒出来自我拯救。这些阴山草场上的种子是杀不死的。
他满怀歉意地离开高府,心中又怀着一丝期待——长孙氏的第二代大多纨绔,这两颗被随意丢弃在山崖间的野草籽是否会开出不异样的花呢?这样想来,没能接回侄子侄女的遗憾似乎也没有那么深重了。
终南山的高氏别业成了一群少年总论天下的隐秘之处。高士廉是一个完美的倾听者——忘年交、师长、父亲三个角色在他身上完美融合、并行不悖。
高士廉发自内心地欣赏唐国公李渊的次子李世民和三子李玄霸。李世民此时正随父亲前往涿郡。李玄霸成为了高府常客。这是一个腼腆的十五岁男孩,气疾几乎毁掉了他练习骑射、追逐祖辈荣光的一切可能。
“但是,除却性格与武艺,大德就是另一个毘提诃。”长孙无忌经常在一场少年们势均力敌的时局辩论后这样向青璟夸赞玄霸,“我和毘提诃说好了将来一起去突厥,去西域建功立业,可惜没法带上大德——他这个样子,连狩猎都困窘!”
长孙青璟偶尔会想起玄霸的哥哥——那个可以为了拯救朋友一家蹈火而来的一身苜蓿清香的少年,那个为了博贪嘴女孩子一笑徒手碎核桃的顽皮少年,那个因夜不归宿而害怕被兄长责罚而慌乱不已的可爱少年。
听着长孙无忌絮叨,她也禁不住臧否起人物来:“李世民虽然爱说大话,仍不失为赤诚君子。”
她不经意回想着李世民前往涿郡时与高士廉和长孙无忌告别的情形。在记忆的隐秘之处,似乎有过一丝担忧与不舍。
“你是说毘提诃还是大德?”无忌转动着猞猁一样的眼珠打趣道。长孙青璟一时语塞,不过她很快从窘境里解脱出来:“你说他们兄弟两个平时当面闲谈时会不会觉得自己在照镜子?”兄妹俩会意地露出一模一样的狡黠笑容。
“不过,毕竟世民的见识比玄霸多一些,他父母游宦在外总是带着他世民从涿郡回来就好了。”无忌整理着与好友的信札,充满期待地说道,“啊,他一定有太多信札里装不下的话要说给我们听,高句丽前线的战事啊,督粮的艰辛啊,运河的工地啊,燕赵的民风啊……他可是一张活地图和话匣子!”
有些人离开大兴很久了,但是一直野蛮地活跃在大兴少年们的话题里。
大家喜欢他,崇拜他,想念他,学着他的语气说话,把他扔进自己的处境里仿拟无坚不摧的人生,又把自己丢进他的处境里幻想一场惊心动魄冒险——最终还是盼着他早点回来。这个无处不在的幻影俨然是少年们的精神领袖。
“等高句丽的战事结束了,杨玄感的叛乱平定了,世民就会平安从涿郡回来了。就这个国家就会又一次归于正常。”长孙无忌渴盼回到那个井然有序的时代,不愿意相信那个时代已经和意气风发的父亲一同随风逝去了。
李家的三公子对于自己的未来规划有一种偏执的热情。他喜欢高府这个可以倾吐自己稚嫩的、宏伟的、不切实际的理想的地方。他认真地提着束脩上门拜高士廉为师。高士廉教授李玄霸经史,也不刻意摆出老师的架子故弄玄虚与恫吓这个天资颖慧的少年。孩子们有大把的时间弈棋、赋诗、骑射。
青璟不会刻意回避玄霸,但一般也都选择在无忌跟前与他简单寒暄几句。偶尔在下棋时听少年们闲谈。大家偷偷传唱着知世郎大逆不道的歌谣,谈着辽东的惨状,对杨玄感和李密的叛乱,在嫌恶讥嘲之中带着一丝欣羡。大家窃窃私语:“这个混乱的世道到底是谁造成的?大兴城的歌舞升平还能够持续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