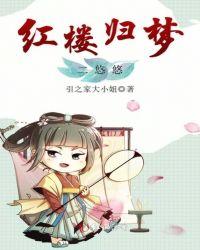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胆小鬼的回响 > 7080(第16页)
7080(第16页)
在学校组织的一次公益活动上,徐以安认识了在读心理学的学妹———季瑾溪。
自来熟的季瑾溪为人真诚,性格又好,而且还懂心理学,很快便成为了徐以安唯一的朋友。
在季瑾溪的帮助下,徐以安的病情控制的很稳定,后来遇到了有鲜活生命力楚怀夕,她慢慢学会了接纳真实的自己。
尽管病情仍会反复,尽管父母依然选择性失明,但她终于有了为自己而活的勇气。
可谁能想到,三个月前还一切向好的诊断报告,在遭遇患者死亡、母亲昏迷、医疗事故和感情破裂的连环打击后,彻底成了废纸。
回忆戛然而止。
看到徐以安和初遇时几乎一样的状态,季瑾溪忍不住拔高声音,质问道,“你为什么就不能反抗你那自私的父母?为什么要一直妥协?!”
徐以安抿了抿唇,“我也想知道为什么。”
季瑾溪一噎,眉头皱的更紧。作为专业的心理医生,她其实知道徐以安是因为什么。
即使徐以安意识到了父母的情感忽视,但她潜意识里仍在不断寻求父母的认可。为了缓解父母不爱自己与父母是养育者的认知矛盾,她将父母的情感忽视美化为他们只是不懂表达爱。这种认知扭曲保护她免于直面被抛弃的创伤,却也使她持续困在自我欺骗的牢笼中。
而长期遭受父母的情感暴力与控制,使她形成无论如何努力都无法改变现状的认知定式。这种低自我效能感不仅削弱了她主动脱离家庭的能力,更导致她在面对新环境时产生泛化的无助。
即使成年后她具备了独立生活的能力,但她潜意识依旧默认反抗是没有用的,就像反复遭受电击的动物,会放弃逃生尝试一样。
再加上孝道伦理构建的社会规训体系对徐以安造成强大的行为约束。对她来说,脱离父母会面临不孝的道德审判,而长期被打压的人会格外在意外界对自己的评价,因此,这种社会评价风险加剧了她的行动阻力。
纵使原生家庭充满痛苦,但作为长期适应的生存环境,反而成为她潜意识里的安全区。这种行为惯性使她在面对改变时产生生理性抗拒,每一次想要挣脱,都像陷入更深的泥潭。
无法与原生家庭和解的小孩,是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大人。徐以安的抑郁是心理、情感、神经生理等多维度因素交织的结果。想要真正的走出来,光靠药物和心理疏导是远远不够的。
和抑郁抗争是一场重塑自我的漫长战役,季瑾溪想,楚怀夕应该能够帮徐以安走出来。
思及此,她滚了滚喉咙,“老徐,我知道你现在内心很煎熬,我也明白你没有勇气从原生家庭的牢笼里挣脱出来,但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和楚怀夕搭建新的安全区”
徐以安闻言猛地转回身,眉目沉沉,“不可以,我和她已经分手了。”
话题被主动提起,季瑾溪趁机追问,“你明明很需要她,为什么还要和她分手呢?”
徐以安愣了半秒,垂眸,避而不答,“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我救不了安安、治不了我妈的病、保不住自己的工作”
顿了顿,她突然笑了起来,笑声里带着挫败与悲伤,“季瑾溪,你说我是不是很没用?”
“不是这样的!你别这样否定自己。”季瑾溪上前一步,却被徐以安抬手制止。
“别用这种眼神看我!”徐以安后退半步,后背又贴上了冰冷的墙壁,深吸了口气,扯出个无奈的笑,“我不需要安慰,不需要怜悯,更不需要你来分析我的心理创伤。”
顿了顿,“你走吧,我会好起来的。”
季瑾溪攥紧指尖,她知道以徐以安目前的心理状况,任何专业的干预都可能被视作攻击。
“你别激动嘛,我只是想说”季瑾溪深吸一口气,“就算你们分手了也可以做朋友,楚怀夕也还是在帮你的。毕竟你们曾经那么相爱”
曾经那么相爱…
曾经…
徐以安喉咙里像是吃鱼的时候卡进去了一根鱼刺一样,吐也不是,吞也不是。
她摇头,“我们从来没有相爱过!”
季瑾溪一愣,眸底闪过一丝不悦,“什么叫你们从来没有相爱过?你不爱楚怀夕?难道不是你主动要和楚怀夕谈恋爱的吗?!”
徐以安抿了下唇,“是我主动开始的,所以我能做的就是让她及时止损。”
“所以你真不爱楚怀夕?”季瑾溪不信。
徐以安嗯了一声,“不爱。”
季瑾溪凑近,一眨不眨地盯着徐以安,“不可能,你明明对她很不一样。”
徐以安盯着自己被水打湿的鞋尖,像是被抽走了所有力气,话说的很慢很慢,“我对她好是因为我想利用她,想利用她找到自我价值,想利用她逃离原生家庭,可是后来,我发现她似乎也没什么用,更何况…现在我手抖得连手术刀都拿不稳,拿什么去爱人呢”
顿了顿,她抬眸看向季瑾溪,“我这样的人只会把身边的人拖进深渊。所以我想明白了,既然不爱她,就不要再自私的利用她了。”
真话和假话混在一起,季瑾溪也有点分不清这人到底爱不爱楚怀夕。
她看着徐以安眼底疯狂翻涌的自我厌弃,不忍心责怪她,往前迈了一步想抱抱徐以安,却在看到对方下意识瑟缩的动作时,生硬止住脚步。
“老徐,你不要这么悲观。你并不是在身边的人下水,你只是需要别人的帮助。”季瑾溪尽量让声音保持平静,“就像当年你需要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