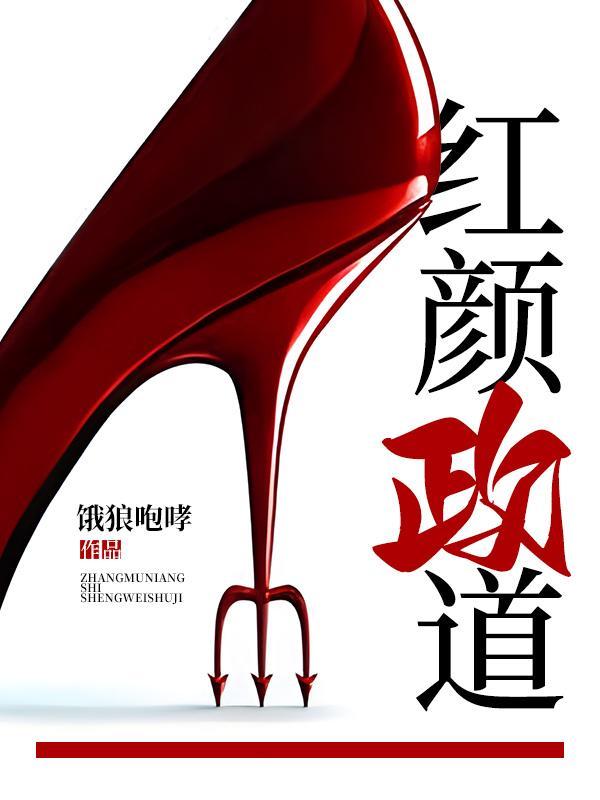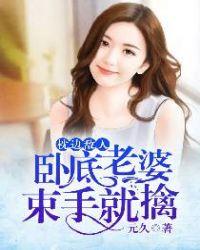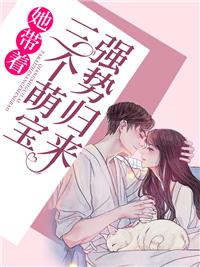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死后情敌为我守寡 > 4050(第12页)
4050(第12页)
沈彻闻点头。乐书音自登基后便投身政务,甚至直到曾经去世,都未曾有过后妃。他似乎把自己悉数奉献给了江山社稷。
“书音是个好皇帝,但我相信,自己也不会差。”太子说道。
沈彻闻单膝下跪:“殿下,您会是大燕最好的君主。”无论未来如何改变,无论十九岁的自己是否会有暂时犹豫和彷徨,沈彻闻始终相信乐书乾会是天下最好的主人。
私心也好,意气也罢,沈彻闻从始至终都这么坚信着。像相信父亲无所不能一样,相信着自己的兄长。
“你能这样想,我很高兴。希望你不会认为我在抢夺属于书音的权柄。”太子弯身,将跪地的沈彻闻扶起,“我无意与他争夺什么……只是,即便为了保护东宫上下,我也不能坐以待毙。”
“这些本就是你的。”沈彻闻说。
太子却摇头:“世上英雄本无主,我仗着什么呢,不过仗着比他早出生几年,父亲多宠爱了几分。但虽然不是我的,我也不会让给他什么,各凭本事而已。”
沈彻闻想,这就是自己即便在乐书乾死后多年,依旧只认这一个主的缘由。
乐书乾温柔却不寡断,宽仁却有野心,会把自己装得无坚不摧却也愿意在信任的人面前坦诚自己的软肋。
“不过。”太子说,“如今二弟复活了,你在十年后,恐怕也是举步维艰吧?”
沈彻闻:“是有些小麻烦,不过也能解决。还好提前叮嘱过那小子,不要脑门一热把这些事告诉老二。”
沈彻闻终于明白,当初自己告诉太子,想先救乐书音,再与乐书音一起救下他时,太子欲言又止的神情到底意味着什么了。
人都会有私心,乐书音也不例外,他不会甘心放弃皇位,只为还大哥一个清白……尤其是,这次回来沈彻闻才发现,老二和太子之间,不知为何有了隔阂。
太子变得小心翼翼,似乎总在讨好忍让。而乐书音性格越发古怪,甚至几次差点当众让太子下不来台。
在原本正常的时空里,这些隔阂肯定也是存在的,只是十九岁的自己太粗枝大叶,连两人间这种细微的变化都没有发现。
“也不能把所有事都推给你,再给我更详细讲一遍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吧。”太子笑笑,“从今天往后的十年间,所有跟我有关的事,务必详细告诉我。父亲与我,不是简单的栽赃陷害可以离间挑拨的,当中必然发生了动摇我们之间信任根基的事。”
沈彻闻眨了眨眼,强迫着自己去仔细回忆那段往事。
那是天授十六年秋天的一次大朝会,文武百官悉数在场,本与往常别无二致。
只是邻近下朝时,突然有官员提出,如今社稷已定,四海皆服,而太子生母仍旧无名无姓未有名分,于礼法不合。
于是百官叩请圣上追封太子生母为后,迁葬入皇陵,以正宗庙。
其实百官也不知太子生母为何人,甚至是生母还是生父,都不知道。太子本人也对此一无所知。
太子虽最得皇帝宠爱,其生身之人的身份却是本朝禁忌,圣上的一块逆鳞,无人敢触碰分毫。
昔年天下初定时,也有人提出过太子生身之人身份不详不宜立为储君。
那人后来被流放边疆,全族三代内不许入朝为官。
自此后,再无人敢置喙太子身世。
只是没有想到那天,竟又有人冒着拖累全族的风险提了出来。
后来沈彻闻也想过,那人或许是被买通,只是为了引出往后一连串的变故。
第47章天授十四年沈彻闻笑自己,经历了这么……
追封太子生母的话刚出口,便引来百官一片附和。
“陛下不愿告知天下太子生身之人,也不愿将太子记入其他妃嫔名下,日后史书会说太子来路不明,便是为着太子,陛下也当三思!”
“微臣不知太子生母昔年因何触怒陛下,但望陛下念在其诞育太子,于宗庙涉及有功的份上,宽恕一二,便是不入皇陵,也该有个位份,否则百姓议论起来,以为天子薄情,又当如何?”
许是有人在其中推波助澜,朝堂之上一时间议论纷纷。
皇帝突然止住了朝中议论,朝太子问道:“此事我儿如何看待?”
太子上前,朝皇帝恭恭敬敬行礼,思忖再三说道:“儿臣觉得,父亲未曾追封生我那人,必有父亲的缘故。只是……儿臣自幼只见过父亲一人,有时也想知道,另一位血脉至亲到底是……”
“够了。”乐宿齐压着嗓音开口,与嗓音一道被压抑到极点的,还有他的怒气,“我说过,我与那个人早已恩断义绝,你是我一个人的孩子,从未有过什么生身之人。”
沈彻闻猜测,皇帝与太子父子二人似乎在那天就走上了岔路的两端。至此君臣父子,背道而驰。
紧接着便是落叶扑朔,凛冬悄至。皇帝接到密奏,说太子私下调兵,打算营救奉安公。
奉安公是前齐废帝,归降大燕后皇帝赐爵奉安公,将其奉养宫中。表面奉养,实则囚禁。自前齐灭国已有十八载,奉安公囚于知恩宫,一步未曾离开。
皇帝拿到密报后,立刻派人调查,竟查到了沈彻闻麾下有调兵痕迹,不由分说便以谋逆的名头将太子软禁东宫。沈彻闻也因此遭到圈禁,连辩白的机会都没能得到。
直到天授十七年初一当夜,太子万念俱灰逝于东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