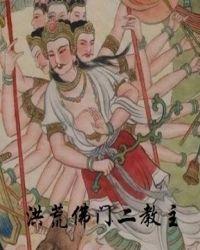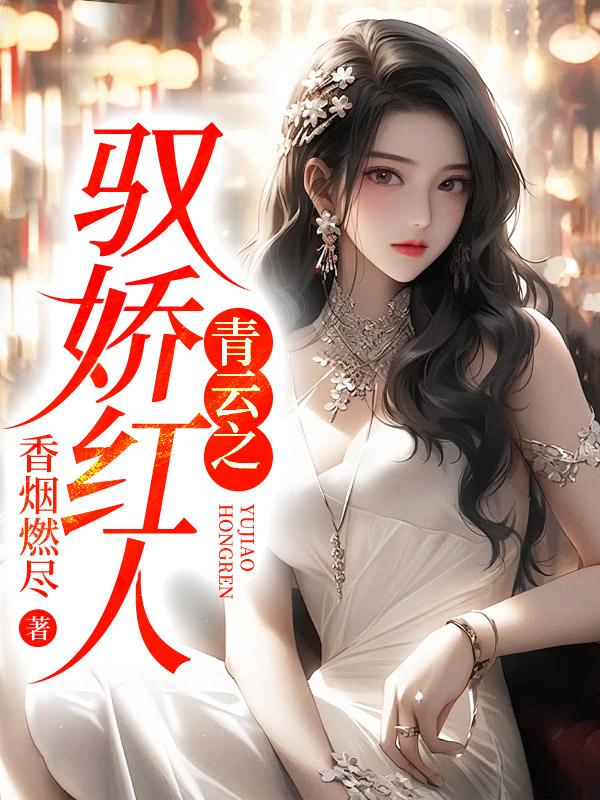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草芥称王 > 第123章 大兄的执着(第1页)
第123章 大兄的执着(第1页)
杨灿侧躺在牛车上,缓缓举起了双手。
牛车旁站着一个少年,不过十七八岁。
月白锦袍、肤色胜雪,腰间玉带扣着一枚羊脂白玉佩。
斜挂的短剑鞘上錾着细密的云纹,一眼看去,便是贵气逼人。
。。。
沙丘之下,钟芽微颤,那缕声波如游丝般穿行于地脉之间,越过冻土、荒原、断城残垣,最终落入一座偏僻小镇的土屋之中。屋内,一个十岁男孩正蜷缩在草席上,额头发烫,呼吸急促。他梦见自己站在无边的白幡林里,脚下是无数张被撕碎的脸,耳边有千万人低语,却听不清一句完整的话。突然,一声清亮的童音穿透迷雾??“我记得!”
男孩猛地坐起,冷汗浸透衣衫,胸口剧烈起伏。他环顾四周,确认自己仍在家中,才缓缓松了口气。可那一句“我记得”,仍在他脑中回荡,仿佛不是出自梦境,而是某种深埋血脉的召唤。
次日清晨,男孩偷偷翻出祖母压箱底的一本破旧账簿。封皮早已褪色,内页夹着半片干枯的槐花。他曾听母亲说,这是外曾祖父留下的东西,但家里从没人敢多看一眼。可今晨,他鬼使神差地翻开第一页,指尖触到纸面的刹那,一股暖流自指腹窜入心口,眼前竟浮现出一段不属于他的记忆:一个穿着补丁长衫的男人,在风雪中背着竹篓行走于山道,篓中藏着一卷写满名字的黄纸。那人每走十里,便停下焚香叩首,低声念道:“阿木、小禾、老吴……你们没死,我记着呢。”
男孩怔住。
他知道,那是外曾祖父,补遗司最底层的抄录员,三年饥荒时因私自记录饿死者姓名而被革职流放。家族讳莫如深,连墓碑都未立。可此刻,那些被抹去的名字,竟随着心跳一一浮现。
他咬破手指,在账簿空白处写下三个字:**我也记。**
这一笔落下,远在千里之外的南山别院,阿启正指导聋哑学子练习手语叙事。忽然,他胸前残存的蝴蝶铃碎片微微发烫。他低头凝视那枚嵌在木匣中的残片,只见原本黯淡无光的铜缘,竟泛起一丝极淡的虹彩。
“来了。”他轻声道。
陈九娘闻声走来,见状眉头微蹙:“又有新种子苏醒了?”
阿启点头:“不止一颗。这次是从普通人心里长出来的。”
他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静音核心虽毁,但“遗忘之根”并未彻底斩断。它换了形态,潜伏在制度缝隙、教育课本、官府文书之中,悄然删减细节,模糊因果,将悲壮化为平淡,将抗争归为顺应。百姓不说,不是不想,而是渐渐觉得“本该如此”。
而今,唯有当一个人主动选择记住,并愿意以血肉之躯承载记忆时,那粒沉睡的水晶种子才会回应。
三个月后,江南某县爆发“失语症”疫病。数百名书塾学生同日失声,医者束手无策。奇怪的是,这些人并非不能发声,而是每当试图讲述过往经历,喉咙便如被铁钳夹住,继而头痛欲裂,昏厥倒地。监察院派员调查,称其为“情绪性喉闭症”,建议禁读史书、减少思虑。
消息传至南山,阿启立即动身南下,携阿念与两名新生代书记生同行。临行前,他在《草芥录》续编扉页添了一句批注:“记忆非藏于纸,而在敢于开口之人舌上。”
抵达该县当日,正值春祭。按例,孩童需背诵《圣谕十六条》,其中有句“遵王法,守本分,毋妄言”。阿启混入人群,见一七岁女童登台,刚念至“毋妄言”三字,嘴角忽然渗血,整个人僵立不动。台下官员急忙命人拖下,对外宣称“偶感风寒”。
当晚,阿启夜访女童家。其母战战兢兢开门,只肯让众人站于门外说话。她说女儿自幼聪慧,最爱听老人讲古,常问“从前真的有战争吗?”“为什么我们家没有族谱?”近日她偷偷抄录祖辈口述片段,昨夜梦中大哭惊醒,醒来便说不出话。
阿启请她取出女儿所写文字。纸上歪斜写着几行小字:
>“太爷爷说,五十年前这里闹过人吃人的事。
>村口老井底下埋着三具小孩骨头。
>县志写‘万民同心渡厄’,可妈妈说,那时候没人管我们。”
>“我想告诉别人,可每次想说,心里就像压了块冰。”
阿启闭目良久,忽而伸手探入怀中,取出一只触感铃。这是他近年专为聋哑人设计的新器,外形如莲苞,内部镶嵌七枚微型振子,能将语言转化为不同频率的震动波,直抵掌心神经。他将铃置于女童额头,默念三遍她写下的文字。
片刻,女童睫毛轻颤,口中发出一声模糊的“啊”。
陈九娘迅速施针于其哑门、通里二穴,又以特制药膏涂抹喉部。约半个时辰后,女孩睁开眼,第一句话竟是:“井……井里还有声音。”
众人悚然。
次日凌晨,阿启率队前往村口老井。当地里正带人阻拦,坚称“此井已封百年,动之不祥”。阿启不语,只命书记生当场朗读《草芥录》中关于“掩埋真相”的章节。随着文字流淌,围观村民中有十余人突觉耳鸣,继而双手抱头,痛呼出声:“我想起来了!我想起来了!”
混乱中,有人自发搬开井盖石板。
井底积水泥泞,漂浮着腐朽木桶与碎布条。阿启亲自垂绳而下,在淤泥深处摸到一块刻字青砖。拭净一看,上面赫然写着:
>“壬戌年四月,饥民赵氏夫妇食子,非恶也,实无活路。吾亲见之,不敢忘。??监粮吏周某绝笔”
砖角还刻着一行小字:“若后人见此,请替我说一声对不起。”
消息迅速扩散。短短七日,周边八县陆续挖出类似证物:藏于墙缝的血书、埋于树根下的骨片铭文、甚至有老农在翻修田埂时掘出一口陶瓮,内盛百余名遇难者名录,字迹娟秀,应是女子所书。
一场沉默百年的倾诉,正在土地深处苏醒。
然而,朝廷反应出乎意料。礼部联合国史馆发布《正风俗诏》,宣布将设立“清源学堂”,专门收容“受虚假记忆影响者”,通过“正音导引术”恢复心智健康。诏书强调:“历史自有定论,私录杂言易惑民心,宜加甄别。”
阿启冷笑:“他们又要开始了。”
果然,不出半月,各地出现身穿灰袍的“清源师”,手持铜磬,每逢集会便敲击三响,宣称可“涤荡妄念,回归清明”。凡参与聆听者,短期内确觉心神安宁,不再纠结往事。但数日后,不少人开始遗忘亲人旧事,或将痛苦经历解释为“必要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