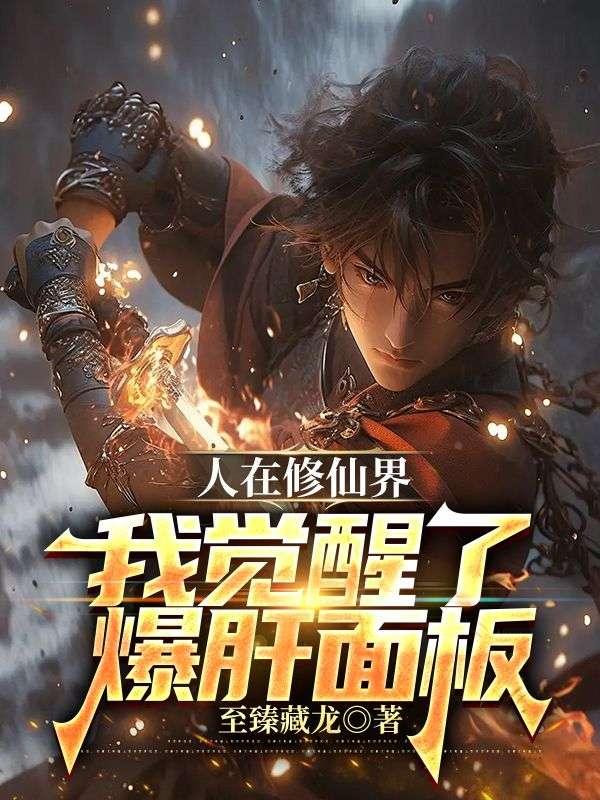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四合院:签到系统让聋老太暴毙 > 第346章 346(第3页)
第346章 346(第3页)
涩度因提前准备才勉强忍住,而始作俑者沈娜,此刻脸色惨白,尷尬至极,心中绝望:“我的名声,全毁了!当眾表演『人体喷泉,我还有何脸面活在世上?天啊,让我死吧!”
想到无需再受石头折磨与高压束缚,沈娜猛地从床上跃起,迅速向车厢一隅奔去。
她经过之处,水珠点点落下,匯成一条曲折的水跡,难辨那是泪水还是其他,或许两者皆有。
见沈娜离去,刘思慧担心闺蜜,急忙追隨其后。
段文斌虽呕吐不止,双腿无力,面色苍白,却也明白此地不宜逗留,需儘快更换衣物,於是也跟隨刘思慧而去。
涩度见状,调侃道:“跑这么快?难道刚才的病是装的?”他自言自语,庆幸自己未中计,“某些人可要倒霉了,不仅没赚到床位费,还被迫享受了『特別的热水澡。”他摇头笑道,“那味道,真冲!”
这话让下铺的一位尖脸青年面色铁青,內心苦涩,虽未真吃异物,却也遭遇了不堪之事。
望著凌乱的床铺与不断滴落的水珠,他满心无奈。
本想戏弄抢铺之人,却反害了自己,床铺被毁,无处安身。
此事闹大,连列车主任都被惊动。
望著车厢內的乱象与刺鼻气味,列车主任惊愕不已,隨即安排涩度等人转移至其他车厢,隨后进行彻底清理消毒。
涩度未参与后续事宜,只是听闻赵刚提及,那几人被罚款,沈娜最多,被罚三十元,其余呕吐者各罚十元。
赵刚笑称,这是他多年火车生涯中首次遇见如此离奇之事,床铺湿透,水珠如帘,即便多次消毒,气味仍刺鼻。
赵刚玩笑道:“常言道女人似水,他却不以为意。”
“经歷此事,他深信不疑!女人不仅是水,更是复杂难测之水!”
幕后叶大官人感慨:“当时稍显急躁,压力未至极致,否则场面定更震撼!”
插曲一幕,段文斌的罚款由刘思慧代缴,非因二人关係,实乃段文斌钱財尽失,835块2毛分文不剩!
段文斌决心寻回失款,初疑落於换衣时的垃圾中,遂翻垃圾桶,脏衣寻回,钱却无踪,最终只能借钱缴罚。
某叶姓青年边数钱边言:“活该!谁让他口无遮拦?此乃报应!”
另一位言语不逊的青年也未逃脱,叶姓幕后以引发事端的小石头“废物利用”,偽装结石塞入其体內,日后必受折磨。
沈娜未丟钱,但钱財遭水浸湿,晾乾后仍留黄渍,叶姓青年婉拒,认为此类钱財难以消受,留给沈娜自行处理。
隨后两日异常平静,几人或许自觉顏面扫地,未再打扰涩度,使其享受了两日悠閒时光,也是他穿越以来最轻鬆的日子。
直至火车到站,再见几人,皆显憔悴。
涩度一行人前往之地乃白山黑水兴安岭的白家寨。
地偏路远,下火车后需乘大巴至最近县城。
路途顛簸五小时,方抵县城。
车站已有眾多接知青人员等候。
下车后,涩度等人被各村寨接送知青的人员呼唤著。
有人高喊:“兴隆村的知青来这里!”“古北村的来这里!”“顽石寨的来我这里集合!”隨后,白家寨的呼喊声传来,涩度一行连忙上前。
“你好,我们是白家寨的知青,请问你是来接我们的吗?”他们面前站著四人,一个体格健壮的中年人和三个青年,全都背著长枪,显得不好对付。
中年男子审视了他们一番,平淡地说:“我是白家寨生產队队长,姓石。”他指了指身旁的人,“这是我们的队员。”接著,石队长告知他们共有六名知青被分配到白家寨,並要求他们自我介绍以確认身份。
段文斌首先开口:“我叫段文斌,来自京城。”隨后是贾梗、贾当、刘思慧、沈娜,每个人都报了自己的名字。
每当有人报名,石队长都会抬头核对,並在本子上记录。
轮到涩度时,她爽快地说:“我叫涩度,也来自京城。”石队长抬头看了看她,眉头微皱:“你叫涩度?”涩度点头,不解其意。
石队长催促道:“你的其他行李呢?快拿来,我们人数点完就要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