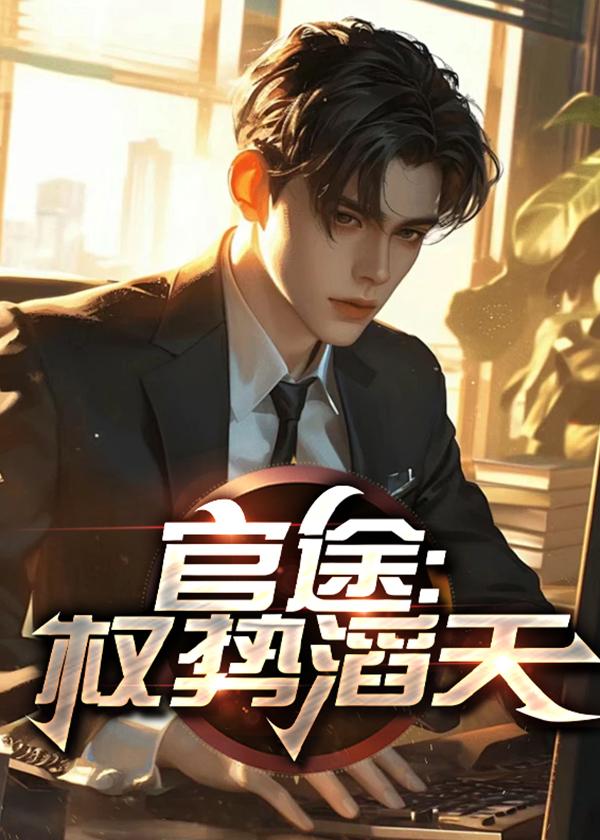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她的字,我的戏 > 尘封的伤疤 言语的利刃(第1页)
尘封的伤疤 言语的利刃(第1页)
林夕的怀抱很温暖,像一座抵御外界风雪的坚固堡垒。但我(苏晴)靠在她怀里,却感觉自己的内里正在一寸寸结冰。网络上的恶评如同鬼魅,在我脑海里盘旋不去,与那些早已被时间尘封、却从未真正愈合的旧伤产生了可怖的共鸣。
那些关于“病秧子”、“神经病”、“不正常”的辱骂,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打开了我记忆深处那扇锈迹斑斑的门,释放出了被封存已久的、来自遥远过去的幽灵。
我猛地颤抖了一下,抱紧我的手臂立刻收得更紧。
“冷吗?”林夕的声音带着未散的鼻音,在我头顶响起,充满了担忧。
我摇了摇头,却说不出话。不是身体冷,是心里冷,冷得刺骨。
那些我以为早已被遗忘、或者至少已被成长磨平棱角的记忆,此刻清晰地、带着当年同样的羞辱和刺痛,汹涌回潮。
中学时代。那是我双相情感障碍初露端倪,却又被所有人(包括我自己)简单归结为“性格孤僻”、“想太多”的晦暗时期。也是我外貌上最……不堪回首的阶段。
青春期荷尔蒙的失调,加上情绪低谷时无法自控的暴食,让我的体重一度失控。我戴着厚重的黑框眼镜,试图遮挡因为失眠和哭泣而浮肿的眼睛。最要命的是那一口参差不齐的牙齿,拥挤,甚至有些微凸,让我即使在不说话的时候,也总是不自觉地抿着嘴,显得更加阴沉和怪异。
我就是以这样一副形象,走进了那所号称重点、实则人际关系同样残酷的中学。
我没有朋友。我的沉默寡言和古怪行为(时而极度低落趴在桌子上一整天,时而又会因为某个微不足道的点而异常兴奋、喋喋不休),让我成了班级里的“异类”,一个完美的、不会反抗的靶子。
霸凌并非肢体上的。那些家境优渥、面容姣好、早早谙熟成人世界规则的少男少女们,有着更“高级”、更伤人的武器——语言。
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那些刻意压低的、却清晰无比的声音,便如同魔咒般在我耳边响起:
“看那个苏晴,又胖又丑,还整天阴着张脸,跟谁欠她钱似的。”
“嘘,小声点,听说她脑子有点问题,会突然发疯的。”
“你们看她那口牙,啧啧,像不像动物园里的……那个?”
于是,我有了一个伴随我整个中学时代的外号——“牙擦苏”。(注:这里借用了一个广为人知的、带有贬义和嘲弄意味的龅牙角色形象,以增强画面感和伤害性)
他们不会当着我的面大声叫,总是在我经过时,故意凑在一起,用恰好能让我听到的音量“窃窃私语”,然后爆发出一阵心照不宣的、刺耳的笑声。
体育课分组活动,我总是最后被剩下的那个。仿佛触碰我,都会沾染上什么不洁的东西。
我的课本会莫名其妙地掉在地上,被踩上脏兮兮的脚印。
我课桌的抽屉里,偶尔会出现写着“丑八怪滚开”的纸条。
有一次,我因为躁狂期短暂的精力过剩,在一次班级演讲中超常发挥,逻辑清晰,引经据典,甚至带着一种我自己都未曾察觉的、近乎咄咄逼人的气势。演讲结束后,短暂的寂静中,我听到后排一个男生用不大不小的声音说:“嗑药了吧?这么兴奋。”
一瞬间,所有刚刚因为我演讲内容而投来的、或许带有一丝惊讶或敬佩的目光,立刻变成了了然、鄙夷和更加深重的排斥。
我就像一只被剥光了皮毛、丢在聚光灯下的老鼠,无所遁形,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淋淋的羞耻。
我试过反抗吗?也许吧。在日记本里写下愤怒而无力的控诉,在深夜咬着被角无声地哭泣,甚至有一次,在极度抑郁的情绪下,我用小刀在手臂上划下过细细的伤痕,试图用生理的疼痛来掩盖内心的崩溃。
但最终,我选择了最彻底的反抗——更深的沉默,更彻底的封闭。我将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用厚厚的书籍和天马行空的幻想构筑壁垒,试图隔绝外界的所有的伤害。
我拼命学习,因为只有在成绩上,我能找到一点点可怜的、不被嘲笑的尊严。
我也开始偷偷地、近乎自虐般地“改造”自己。我疯狂节食,在家人睡着后偷偷起来跳绳,直到虚脱。我攒下所有的零用钱,在高中毕业后,第一时间去做了牙齿矫正,戴上了漫长的、冰冷的牙套。我学着摘下眼镜,换上隐形的,尽管最初总是流泪不止。
这些改变是缓慢而痛苦的。就像把一棵长歪了的树,强行掰直。过程伴随着骨骼的疼痛和内心的屈辱。
大学后,牙套终于摘掉了。体重也因为长期的饮食控制和疾病的消耗(抑郁时毫无食欲,躁狂时消耗巨大)降了下来。我学会了用化妆品修饰过于苍白的脸色和浓重的黑眼圈。我留长了头发,它们自然地微卷,能很好地修饰脸型。
当我再次站在镜子前时,里面的人,五官清秀,身材纤细,甚至偶尔会被陌生人夸一句“有气质”。连姜医生第一次见我时,也曾委婉地表示,我的外在条件其实相当不错。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