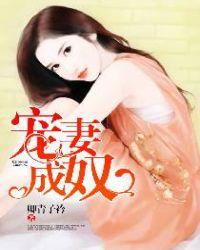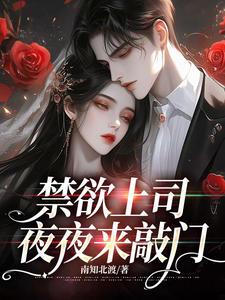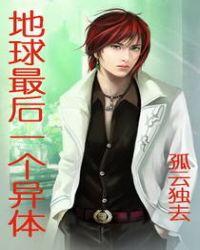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岁时食肆[美食] > 上元篇 祈蚕愿(第3页)
上元篇 祈蚕愿(第3页)
这是一个死循环。这次是侥幸催动,吓退了凡人,下次呢?
但眼下顾不得那么多了。
她走到那小孩身边,蹲下身,轻声问道:“你没事吧?”
姜糖担心得很,放在现代十三四岁还是初中生的年纪,等于是个遭遇了霸凌的可怜小孩。
小孩依旧蜷缩着,警惕地抬起头,脏污的小脸上那双琥珀色的眼睛像燃烧的炭火,竟然是个有着一半胡人血统的孩子。
他死死抱着怀里一个陈旧的小布包,摇了摇头,挣扎着想自己站起来,却因为伤势踉跄了一下。
姜糖下意识地伸手扶住他。小孩身体一僵,却没有推开。
“谢谢。”小孩的声音沙哑,带着这个年纪不该有的低沉。
“你叫什么名字?”姜糖问。
“二狗。”
倒是个好养活的名字,姜糖心想。
“你家在哪儿?我送你回去。”姜糖看着他满身的伤,不放心地说。
小孩沉默了片刻,指了指巷子更深、更破败的方向。
那是一个几乎不能称之为“家”的地方,位于坊市最边缘,是个低矮破旧的土坯房,四处漏风,家徒四壁。
但小孩却熟练地生起一个小小的火塘,烧了点热水,又翻找出一些干净的布条,默默处理着自己身上的伤口,动作麻利得让人心疼。
姜糖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在泥泞中拼命挣扎求生的幼兽。
“你……一个人住?”她试探着问。
“嗯。”小孩头也不抬,“我娘去年病死了。”
姜糖心中后悔问出这个问题。她看着这简陋的环境,又想到自己此刻同样无处可去的窘境,一个念头冒了出来。
她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听起来平静而真诚:“小朋友,你知道,我不是坏人。能不能在你这里借住几天?我可以帮你干活,或者你想让我做什么,只要我能做到,都可以。”
小孩猛地抬起头,那双警惕的眼睛审视着她,似乎在判断她话里的真假。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闷闷地开口:“你会……祈蚕吗?”
“祈蚕?”姜糖一愣。正月十五日不仅是上元节,也是中国古代的祈蚕日,蚕农祈求蚕神保佑,蚕茧丰收。李渔之前给她讲过,奶奶也提过相关的习俗。
《续齐谐记》说:吴县张成夜起,忽见一妇人立于宅东南角,谓成曰:“此地是君家蚕室,我即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当令君蚕桑百倍。”言绝而失之。成如言作膏粥。自此后大得蚕。
“我娘以前养蚕。”小孩低下头,声音低了下去,带着一丝哽咽,“每年这个时候,她都会按规矩祈蚕……我想照着她做的样子,再做一次。”
姜糖的心瞬间变得柔软。她看着小孩倔强又脆弱的侧脸,郑重地点了点头:“我会。我帮你。”
姜糖暂时在这个破旧的小屋里安顿下来。
她按照习俗制作膏粥,带着小孩,在月光下,按照古老的仪轨,默念“登高糜,挟鼠脑,欲来不来,待我三蚕老”。虔诚地完成了整个祈蚕仪式。
小孩学得很认真,每一个步骤都力求与他记忆中母亲的身影重合。
当仪式完成时,他望着夜空,久久不语,但那紧绷的肩线,似乎柔和了一些。
在这个过程中,姜糖也清晰地感受到,当她主动运用司历的知识去完成这些与岁时相关、充满诚心正念的仪式时,她与司历尺之间那种玄妙的联系,似乎变得更加清晰、也更加紧密了。
羁绊越深,责任越重,也越容易被卷入非凡事件之中。这仿佛是一个无法逆转的循环,但起码在此刻,姜糖感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被需要的力量感。
夜色深沉,破旧的小屋里,火塘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一大一小两个身影,在这千年之前的长安角落,因为一场意外的流落和一场充满思念的祈蚕仪式,命运短暂地交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