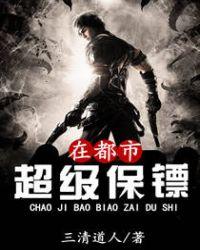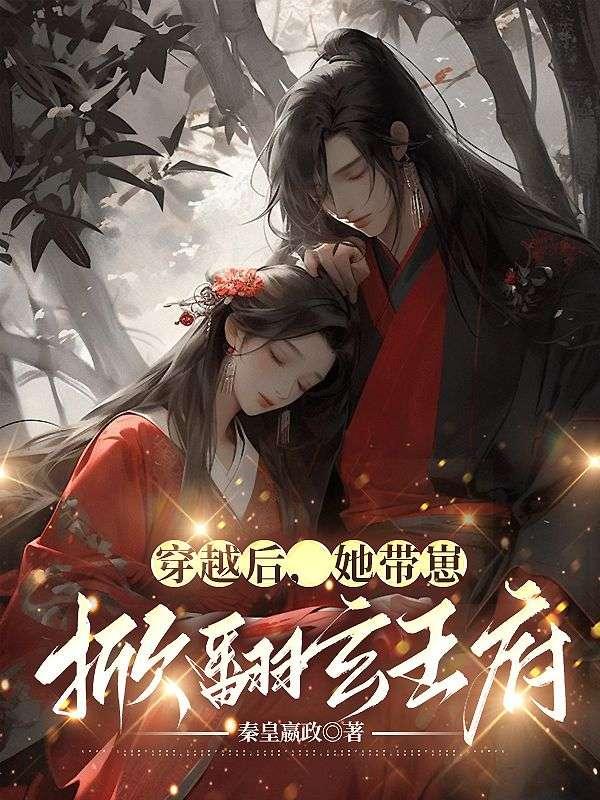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从零开始当山神 > 第 17 章(第2页)
第 17 章(第2页)
如今的李莲已非不谙世事的少女,加之母亲常在身边提点,她自然明白赵小苗执意让阿兰担任庙祝的深意——那是在这纷扰世间,为这拥有惊人美貌却无法言语的外孙女,寻得一处稳妥的庇护所。
看着阿兰灵秀的身影,李莲心中一动,转向祝媱道:“师父,阿兰天资聪颖,心思纯净。若是她能一同学习草木知识,领悟的速度定然远胜于我。”她顿了顿,语气带着试探与期盼:“所以师父……您是否同意我的提议?”
祝媱收回目光,看向身旁目光灼灼的弟子,自然明白她所指为何。她微微一笑,语气平和却带着肯定:“既然你心中已有成算,那便依计而行吧。”
师徒二人此刻商议的,正是关乎传道大业的关键一步。此事源于李莲不久前的青柳县之行。那日,她本为寻访识字夫子而去,却在踏入县城后,先被药铺里熙攘的人群和琳琅的药柜所触动,后又闻得学堂中传来的朗朗书声。
归来后,她独坐沉思:若仅凭自己一人埋头苦学文字,何时才能将师父所授的浩瀚知识整理成册,传于世人?纵然是上古的华胥氏,亦非凭一己之力识尽草木,而是汇聚众人之智,刻碑流传。反观自身,在巫山潜心修习半月,真正能烂熟于心的草木特性,不过寥寥。若想达成师父“辨识十二万九千六百五十七种草木,并熟记其十二分之一”的出师要求,单打独斗,何其艰难?
深思熟虑后,一个崭新的念头在她心中清晰起来:师父怀有慈悲之心,愿将草木知识普惠众生。既然这样,我何不一边学习一边传道呢?
虽然心中已经有了清晰的规划,李莲还是希望得到师父的亲口应允。对她而言,这不仅是对计划的认可,更是一种来自神明的指引和祝福。
而祝媱,自然是认同的!
事实上,第一次当神的祝媱,内心时常会有种一种微妙的拉扯。一方面,她努力维持着神祇应有的高深莫测与超然物外,时刻提醒自己言谈举止要淡然,要有格调。可另一方面,一个更真实的声音在她心底叫嚣:我都已经是神了,难道还不能随心所欲一点吗?何必总端着架子?
当李莲提出要去县城学习文字时,祝媱几乎是恍然大悟,如同被点醒了某个沉睡的记忆!她脱离校园多年,竟险些忘了知识传播最高效的途径是什么——那便是满足人的切实需求!
她可是从千军万马的高考中杀入985名校,在职场上也从未停止过学习提升的人啊!她太清楚了,人在什么时候会对知识产生最强烈的渴求?绝不是被动灌输之时,而是当人明确意识到这些知识能解决自身困境、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之际!
李莲提出的“边学边传道”的思路,恰恰暗合了这一点。将草木知识与治病救人、改善生计紧密联系起来,让人们自发地产生学习的动力,这远比空泛地宣扬神迹要高明得多,也持久得多。
于是,祝媱压下心中那份“本神早就该想到”的微妙尴尬,维持着淡然的姿态,给予了李莲肯定的答复。她看着弟子眼中闪烁的、因得到认可而愈发坚定的光芒,心中也不由得升起一股期盼。
但想法虽好,实践起来却步步维艰。
李莲构思的“巫山学堂”计划,首先便卡在了最基础的人选问题上。
她设想能像城里夫子开学堂那般,招收一批学生来巫山系统学习草木知识。可巫山在哪里?在层峦叠嶂的深山腹地!寻常人连进山都需鼓起勇气,又有谁会愿意长途跋涉,深入这莽莽山林,只为学习一些听起来虚无缥缈的“草木要义”呢?
李莲不甘心,连续三日前往青柳县,在集市、街巷向人宣讲,言明自己是奉巫山娘娘法旨,向人间传授辨识草药、治病救人的知识。然而,任凭她说得口干舌燥,换来的多是怀疑的目光、不以为然的摇头,甚至几声嗤笑——“巫山娘娘?哪个山旮旯的小神?”“小姑娘,莫要胡言乱语了。”
无奈之下,她只得拖着疲惫的身躯翻山越岭返回下河村。路上,她冷静下来思考失败的原因,渐渐明白了关键:对于青柳县的人而言,“巫山神女”这个名字陌生得很,既无显赫庙宇,又无广为流传的神迹故事,凭什么让人相信并追随?人们只会当她是个宣扬乡野小神的疯癫女子。
李莲意识到,要想让外界接受,必先让巫山娘娘的声名传播出去。她立刻行动起来,挨家挨户召集村民,希望大家在去青柳县赶集、走亲访友时,能有意无意地提及巫山娘娘的恩泽与灵验。
然而,她也深知其中的难度。对于亲身经历过瘟疫被神迹拯救的下河村人来说,信仰巫山娘娘是发自肺腑、自然而然的事。可对于那些从未见过神迹的外乡人,巫山神女恐怕与千百个流传在乡野传说中的无名小神并无区别。世人皆言举头三尺有神明,可谁又真正见过神明显灵?让人轻易改信,谈何容易。
这日傍晚,李莲站在村口的晒谷场上,面前是闻讯聚集而来的乡亲们。她看着一张张熟悉的面孔,诚恳地说道:“各位叔伯婶娘,咱们都受过娘娘天大的恩惠。如今我想将娘娘的慈悲传给更多人,让外界也知道咱们巫山娘娘的威名,可在外头,娘娘的名声还不响亮。今日请大家来,就是想集思广益,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法子,能让娘娘的圣名,更快地传扬出去?”
谷场上顿时议论开来,村民们七嘴八舌,有的提议去县里唱傩戏宣扬神迹,有的说可以免费施舍些符水,还有的说干脆把庙会办热闹些吸引外人……李莲认真听着,心中期盼着能从中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