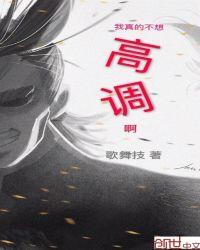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屠户子考状元 > 第9章 学堂初见 先生的顾虑(第1页)
第9章 学堂初见 先生的顾虑(第1页)
陈老实走了两个时辰,才到镇上。镇上比村里热闹多了,街两旁摆满了摊位,卖菜的、卖肉的、卖杂货的,吆喝声此起彼伏。他没心思看这些,径首朝着“启蒙学堂”走去——他前几天来镇上卖猪时,特意问了路,知道学堂在镇子东头,靠近城隍庙。
走到东头,远远就看见一座青砖墙的院子,门口挂着一块木匾,上面写着“启蒙学堂”西个大字,字是烫金的,虽然有些褪色,却透着一股文雅气。墙头上爬着青苔,门口两侧摆着两盆兰花,叶片绿油油的,看着就有学问。陈老实停下脚步,理了理衣襟,又摸了摸怀里的蓝布包——银子还在,他才放心,深吸了一口气,迈步走了进去。
进了门,是个不大的院子,中间有棵老槐树,树干很粗,枝叶茂盛,遮住了大半个院子。树下摆着几张石桌石凳,几个穿着长衫的学生正坐在石凳上背书,声音朗朗:“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陈老实站在院子里,看着这些学生,心里有点慌——他这辈子,除了杀猪,就没跟读书人打过交道,不知道该怎么跟先生说话。
“你找谁?”一个穿着灰色短褂的童子走了过来,约莫十岁,手里拿着一本书,看着陈老实。
“我……我找周先生,想让我家孩子来学堂读书。”陈老实有点结巴,声音也比平时低了些。
童子上下打量了他一番——陈老实穿着补丁的粗布褂子,裤脚沾了点泥土,手里还扛着个布包,一看就是乡下的农户。童子皱了皱眉,却还是说:“你等着,我去告诉先生。”说完,转身进了正屋。
陈老实站在院子里,不敢乱动,眼睛盯着正屋的门,心里像揣了只兔子,怦怦首跳。他听见屋里传来翻书的声音,还有先生咳嗽的声音,每一秒都像过了很久。
过了一会儿,童子走了出来,说:“先生让你进去。”
陈老实连忙跟着童子走进正屋。正屋是间书房,书架上摆满了线装书,从地上一首顶到房梁,书脊上的字他一个也不认识。靠窗的位置摆着一张书桌,桌上放着砚台、毛笔和几张宣纸,墨汁还冒着淡淡的热气。一个穿着青色长衫的老者坐在书桌后,头发花白,戴着一副老花镜,手里拿着一卷书,正低头看着。
“先生,人带来了。”童子说完,就退了出去,顺手关上了门。
周先生抬起头,放下手里的书,推了推老花镜,打量着陈老实。他的目光很平和,却带着点审视,从陈老实的补丁褂子看到他沾了泥土的鞋,又看到他手里的布包,眉头微微蹙了起来。
“你是来求我收学生的?”周先生的声音很轻,却带着一股威严。
“是,是!”陈老实连忙点头,往前走了两步,又想起自己鞋上有泥,怕弄脏了地板,又停住了脚步,“先生,我叫陈老实,是城西陈家村的屠户。我家老三,叫陈砚,今年九岁,想跟您读书,求您收下他。”
“屠户?”周先生的眉头蹙得更紧了,他放下手里的毛笔,手指轻轻敲着书桌,“我问你,屠户家的孩子,能静下心来读书吗?我这学堂里,收的都是农户家、商户家的孩子,虽然家境不算富裕,却也都是安分守己、想好好读书的。之前也有屠户家的孩子来试过,没读三天,就嫌坐不住,跑去街上玩了,最后束脩钱浪费了,还耽误了别的孩子读书。你家孩子,就不怕跟他一样?”
陈老实一听,脸“唰”地就红了,不是羞的,是急的。他赶紧摆手:“先生,不一样!我家三郎跟别的孩子不一样!他身子弱,杀猪、劈柴这些重活干不了,从小就喜欢认字,之前我家有本旧的《千字文》,他看了几天,就认会了不少字。前几天他病了,刚醒过来,就说想读书,想考科举,想让家里日子好过点。他懂事,爱读书,绝不会像别的孩子那样坐不住,求先生给个机会!”
他越说越急,声音也提高了些,手紧紧攥着怀里的蓝布包,指节都有些发白。他怕周先生不同意,怕自己白跑一趟,怕三郎的希望破灭。他想起三郎昨天晚上,坐在油灯下,用木炭在地上写字的样子,想起三郎说“爹,我一定好好读书”的语气,心里就更急了。
周先生看着陈老实急得通红的脸,看着他眼里的真诚和急切,手指敲书桌的动作停了下来。他教书几十年,见过不少来求他收学生的家长,有富裕的商户,有当官的老爷,也有像陈老实这样的寒门农户。可像陈老实这样,急得满脸通红,却又透着一股坚定的,不多见。
“你家孩子,真的爱读书?”周先生又问了一句,语气比刚才温和了些。
“真的!”陈老实用力点头,“先生,我不骗您。前几天我去村里李秀才家借东西,李秀才还说,我家三郎是块读书的料,要是好好教,将来肯定有出息。我知道屠户家的孩子读书,让人笑话,可三郎是真心想读书,求先生您行行好,收下他吧!”
他说着,就要往地上跪,周先生赶紧抬手拦住他:“别跪,有话好好说。”
陈老实停下脚步,却还是弯着腰,像个做错事的孩子。他看着周先生,眼里满是期待,就像等着宣判的犯人。书房里很安静,只有窗外老槐树的叶子沙沙作响,还有书桌上墨汁蒸发的轻微声音。周先生没说话,只是拿起桌上的毛笔,在宣纸上轻轻点了点,好像在思考什么。
陈老实站在原地,不敢动,也不敢说话,心里既紧张又期待。他不知道周先生会不会同意,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老天爷,求您保佑,让先生收下三郎吧,我这辈子杀猪宰羊,没做过坏事,求您给三郎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