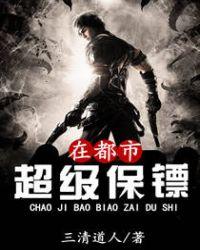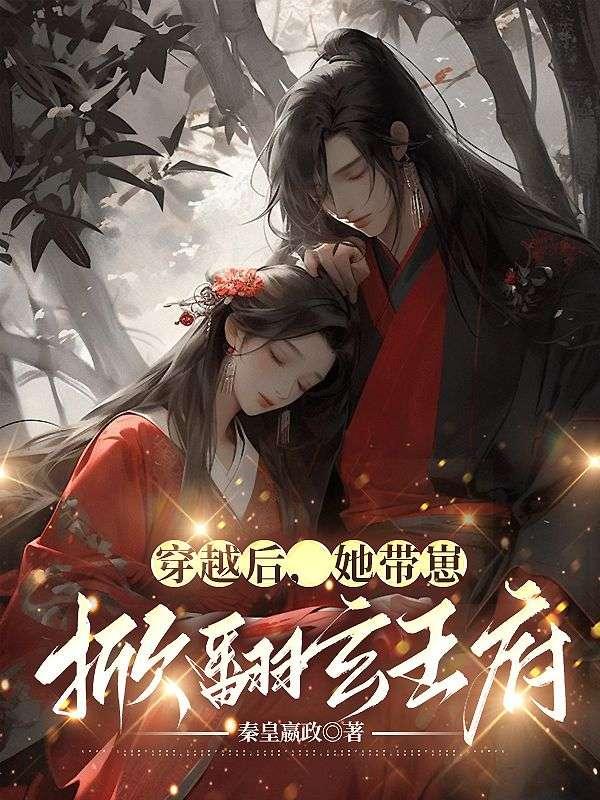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嘉靖榜眼:从流放地到内阁 > 第16章 府试遇吴生考前咳血病发(第2页)
第16章 府试遇吴生考前咳血病发(第2页)
沈砚之却没放手,反而更紧地扶住他:“什么连累不连累的!你都这样了,还想着考试?我这就去找监考大人,让他们请郎中过来!”
“不行……”吴生摇摇头,眼泪从眼角滑落,“我不能取消资格……我要是考不了……我爹在地下……也不会瞑目的……”
就在这时,一个威严的声音响起:“出什么事了?”沈砚之抬头,只见府试的主考官——宁安府知府胡宗宪,正带着衙役和郎中走过来,脸色严肃,正是当年县试时破格允许吴生续考的那位知府。
“胡大人!”沈砚之连忙拱手行礼,“这位吴生咳血病突然发作,还摔在了地上,恳请大人让郎中为他诊治!”
胡宗宪走到吴生面前,蹲下身,仔细看了看他的脸色,又摸了摸他的脉搏,眉头皱了起来:“脉象虚弱,气血两亏,还咳血,这身子怕是撑不住三场考试了。”他转向郎中,“先给他诊治,看看能不能缓解。”
郎中连忙拿出药箱,给吴生施针、喂药。片刻后,吴生的咳嗽渐渐平息,却还是虚弱地靠在沈砚之怀里,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郎中对胡宗宪摇了摇头:“大人,这位考生的咳疾己到晚期,就算暂时缓解,也绝不能再继续考试,否则怕是会有性命之忧。”
吴生听到这话,眼泪流得更凶,却倔强地说:“我能考……我还能考……胡大人,求您给我一次机会……我就考一场……一场就好……”
胡宗宪看着他眼中的绝望与执着,心里也有些不忍。他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是寒门出身,为了考科举,也曾忍饥挨饿、带病备考,深知这份不易。他沉默了片刻,对郎中说:“先把他抬到隔壁的空房休息,好生照料。至于考试……等他醒了再说。”
衙役们连忙上前,小心翼翼地把吴生抬起来,往空房走去。沈砚之想跟过去,却被胡宗宪叫住:“沈砚之,你跟我来。”
沈砚之心里一紧,以为自己擅自离开号房会被责罚,却还是跟着胡宗宪走到一旁。胡宗宪看着他,语气缓和了些:“你可知擅自离开号房,按规矩当如何处置?”
“晚辈知晓,当取消考试资格,”沈砚之低头道,“可吴兄情况危急,晚辈实在无法坐视不管,若大人要责罚,晚辈甘愿受罚。”
“你倒有几分胆识和义气,”胡宗宪笑了笑,“当年县试时,你为吴生代答,虽违规却情有可原;今又为他挺身而出,不顾自己的考试资格,这份心性,比许多只知埋头读书的考生强多了。”他顿了顿,“不过规矩就是规矩,你擅自离开号房,本应取消资格,但若不是你及时呼救,吴生恐怕会有性命危险。本府就破例饶你一次,下次不可再犯。”
沈砚之连忙拱手:“多谢大人!晚辈再也不敢了!”
“回去吧,好好准备考试,”胡宗宪道,“你县试时的策论,本府看过,对‘屯垦戍边’的建议很有见地。府试的策论题,会更侧重府域内的民生问题,你多想想实际解决办法,别只谈空论。”
沈砚之愣了一下,没想到胡宗宪竟看过他的县试试卷,还特意提点他,连忙道谢:“多谢大人指点!晚辈定当谨记!”
回到自己的号房,沈砚之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他看着衣袖上的血迹,想起吴生苍白的脸和执着的眼神,心里满是感慨——他们这些寒门考生,为了一个渺茫的科举梦,付出的代价,远比常人想象的更多。
他深吸一口气,把杂念抛开,拿出《策论精要》和府试真题,开始复习。胡宗宪的话提醒了他,府试的策论不同于县试,更注重对实际问题的分析与解决,他必须结合宁安府的实际情况,提出切实可行的建议,才能在众多考生中脱颖而出。
他翻到“宁安府赋税不均”的真题,想起县试时刘崇文教他的“逐题拆解法”,便在纸上写下:“问题:富户隐瞒田产,贫户无田缴税;原因:清丈不力,官员包庇;解决办法:1。派公正官员赴各县清丈田亩,登记造册;2。严惩包庇富户的官员,公示贪腐案例;3。设举报机制,鼓励百姓举报隐瞒田产者。”
写完后,他又反复修改,补充了“清丈田亩的具体步骤”和“举报奖励机制”,确保建议足够详细、可行。不知不觉间,考试的钟声响起,衙役们开始分发试卷,沈砚之放下笔,深吸一口气,做好了迎接府试第一场考试的准备。
而隔壁的空房里,吴生缓缓睁开眼睛,看着天花板,眼泪无声地滑落。他知道,自己的科举梦,恐怕到此为止了。可他不后悔,至少他来了,努力过了,也见过了像沈砚之这样温暖的人,就算此生再无机会,也没什么遗憾了。
窗外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沈砚之的试卷上,映得他的字迹格外工整。他握着笔,开始认真答题,心里却默默想着:吴兄,你放心,我会带着你的那份希望,一起考下去,就算再难,也绝不会放弃。因为我知道,我们这些寒门子弟的坚持,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所有像我们一样,在黑暗中寻找光明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