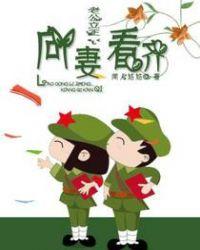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嗅杀 > 第一百八十三章 未尽的硝烟(第1页)
第一百八十三章 未尽的硝烟(第1页)
废弃工厂的行动,在外界看来或许是一次成功的抓捕——两名携带武器、形迹可疑的嫌犯落网。但在韩逸和他的核心团队心中,这无疑是一场惨败。他们不仅没能触碰到“牧羊人”的衣角,反而被对方玩弄于股掌之上,那最后弥漫开来的浓烈汽油味,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抽打在每个人的脸上。
两名被抓的嫌犯是标准的“弃子”。经过连夜审讯,他们只承认是受人雇佣,前来废弃工厂“取一件东西”,至于雇主是谁、取什么东西、爆炸为何发生,一概不知。联系方式和酬金支付方式都是单线的、无法追踪的。线索到这里,再次彻底中断。
海音在酒店得知消息后,沉默了许久。她站在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前,俯瞰着城市璀璨的灯火,心中却是一片冰冷的荒芜。她能想象韩逸此刻的挫败与愤怒,也能感受到那股仿佛能穿透电话线、萦绕不散的邪恶气味。无力感像潮水般再次涌来,但这一次,潮水退去后,露出的不是柔软的沙滩,而是被冲刷得更加坚硬的礁石。
她回到别墅时,天己蒙蒙亮。韩逸坐在客厅沙发上,没有开灯,身影融在灰暗的晨曦里,透着一股浓浓的疲惫。听到开门声,他抬起头,眼里的红血丝更加密布。
“你没事吧?”两人几乎同时开口,问出了同样的话。
随即,是一阵短暂的沉默,然后,两人不约而同地露出了一丝苦涩又带着暖意的笑容。这种在逆境中依旧紧紧相系的默契,是“牧羊人”无法摧毁的。
“我们低估了他。”韩逸的声音沙哑,“他比我们想象的更谨慎,也更……猖狂。”
“但他也暴露了更多。”海音在他身边坐下,语气冷静地分析,“他如此大费周章地示威,说明他感到了威胁。我们重启‘夜莺’案,关联到那种溶剂,确实触动了他的某根神经。他害怕我们沿着这条线查下去。”她拿起茶几上那个装着杜松子精油的喷雾瓶,轻轻喷了一下,清冽的木质香气稍稍驱散了脑海中那令人不快的汽油味。“而且,他这次动用了爆炸物,虽然是为了制造混乱,但也意味着他的行动在升级,这本身就会留下更多的调查线索。”
韩逸点了点头,海音的分析像一剂清醒剂,让他从挫败的情绪中挣脱出来。“没错。爆炸物的来源,那辆无牌车的追踪,还有他这次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而动用的更多人力和资源……只要我们咬死不放,总能找到新的突破口。”他的眼神重新凝聚起锐利的光芒,“‘夜莺’案,那条线不能断。还有那个影子商人,我怀疑,‘牧羊人’很可能就是他,或者与他有极深的关联。”
接下来的几天,风暴似乎暂时平息了。“牧羊人”没有再发送任何信息,也没有新的恐吓事件发生。但韩逸和海音都知道,这不过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平静。对方正在暗处舔舐伤口,或者策划着下一轮更猛烈的进攻。
两人的生活似乎恢复了表面的常态,但某些东西己经悄然改变。海音不再仅仅专注于教学和研究,她开始更系统地将自己遭遇的“气味恐吓”作为特殊案例,融入到司法气味学的研究框架中,思考如何建立针对此类“气味标记”威胁的预警和反制策略。她的内心,那份要将“牧羊人”绳之以法的誓言,变得更加具体和坚定。
韩逸则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对“夜莺”案和跨境影子商人的深挖上,与国际刑警组织的沟通也变得更加频繁。他身上的气质变得更加冷硬,仿佛每一根神经都时刻处于备战状态。他知道,这是一场持久战,一场意志的较量。
一周后的傍晚,海音接到了苏晓的电话。那个敏锐的女学生在电话里语气有些激动:“海老师,我按您课上讲的方法,重新分析了您提供的(匿名处理后的)那段气味描述数据,我发现其中一个酯类成分的波动模式,和我之前在一篇关于东南亚特定区域工业污染的文献里看到过的某种催化剂降解产物的特征很相似!虽然不能确定,但这也许可以缩小那种溶剂的产地或者使用范围……”
海音握着电话,心中波澜涌动。希望,总是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再次萌发。敌人的阴影依旧浓重,但他们并非孤军奋战,前进的路上,正在汇聚起越来越多的微光。
晚上,海音和韩逸再次站在暖房里。新栽种的岩兰草己经服盆,在夜色中舒展着坚韧的叶片,散发着沉稳的根系香气。远处城市灯火阑珊,近处草木无声。
“他还会来的。”海音轻声说,语气平静。
“我知道。”韩逸握住她的手,掌心温暖而有力,“但下一次,我们会准备得更充分。”
夜空下,杜松子清冷的气息与岩兰草沉稳的根香交织在一起,仿佛构筑起一道无形的屏障。第十八卷的故事,在这弥漫着未散硝烟和悄然生长的希望中,画上了一个暂时的休止符。但所有人都知道,与“牧羊人”的最终决战,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