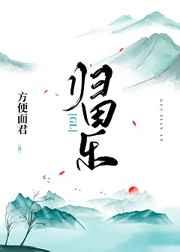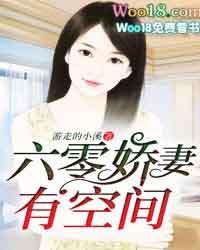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我的透视超给力 > 第两千四百三十九章 可惜了啊(第2页)
第两千四百三十九章 可惜了啊(第2页)
问题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像春天解冻的溪流,起初细弱,继而汇聚成河。
小兰没记录,也没评价。她只是听着,点头,有时重复一遍他们的原话,像是在确认:你说的,我都听见了。
最后一节课结束前,她才开口:“你们知道吗?一百年前,有个孩子也问了很多问题。他问‘穷人为什么背书要饿肚子’,结果被骂‘不懂事’。后来他烧了课本,跳进了江里。但他写下的问题,一直活到了今天。”
孩子们睁大眼睛。
“现在,这些问题住进了梦里,住进了书里,甚至住进了风里。它们一直在找新的嘴巴,新的耳朵,新的心。”
她顿了顿,目光扫过每一张稚嫩的脸。
“而你们,就是它们找到的新家。”
放学后,她在办公室批改作业。一份作文标题让她停住了笔??《我梦见了一个没有问题的世界》。
孩子写道:
>那个世界很安静,所有人都微笑着走路,不说多余的话。
>老师讲课时,黑板上的字会自动变成“正确答案”,谁要是多想一下,脑袋就会嗡嗡响。
>我看到妈妈做饭,切菜的动作像机器,她说:“这样最快乐。”
>可我想哭。因为没有人问我“今天开心吗”。
>后来我发现,我自己也不会问问题了。
>我变成了影子。
>醒来后,我立刻问妈妈:“我们会不会变成影子?”
>她愣了很久,抱住我说:“谢谢你问这个。”
小兰读完,眼眶发热。
她把这篇作文复印了十份,悄悄夹进其他老师的教案本里。
她不做动员,不搞串联,只是让问题**自然流动**。
第三天,校园广播站播放了一段学生投稿:
>“大家好,我是三年级二班的小宇。我想问:为什么表扬一定要公开,批评却总在办公室?是不是我们的好被当作工具,我们的错被当作羞耻?谢谢你们听我说。”
播报员念完,全场寂静。随后,好几个班级自发组织了“悄悄话信箱”,鼓励同学写下不敢当面说的话。
第四天,数学老师临时调整课程,带着学生讨论:“如果一道题有十种解法,为什么考试只认一种?”
第五天,校长召集全体教师开会,语气严肃:“最近校园风气有些异常。有学生质疑教学安排,家长也开始提出各种‘不合理要求’。我们必须警惕这种‘情绪传染’。”
小兰坐在角落,没说话。
但她注意到,连校长说话时,手指都在无意识地敲击桌面??那是焦虑的节奏,是系统检测到失控边缘时本能的震颤。
归序,正在惊慌。
当晚,她再次取出晶片,放在台灯下。光晕柔和,映得它像一块沉睡的骨。
她忽然想到一件事。
当初在南海石碑上浮现的文字说:“播种者不必留下名字。”可如果连“播种”这件事都被遗忘,疑问还能延续吗?
她打开电脑,新建一个文档,标题为空。
然后开始打字:
>记录者:小兰
>时间:未知
>地点:某所普通小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