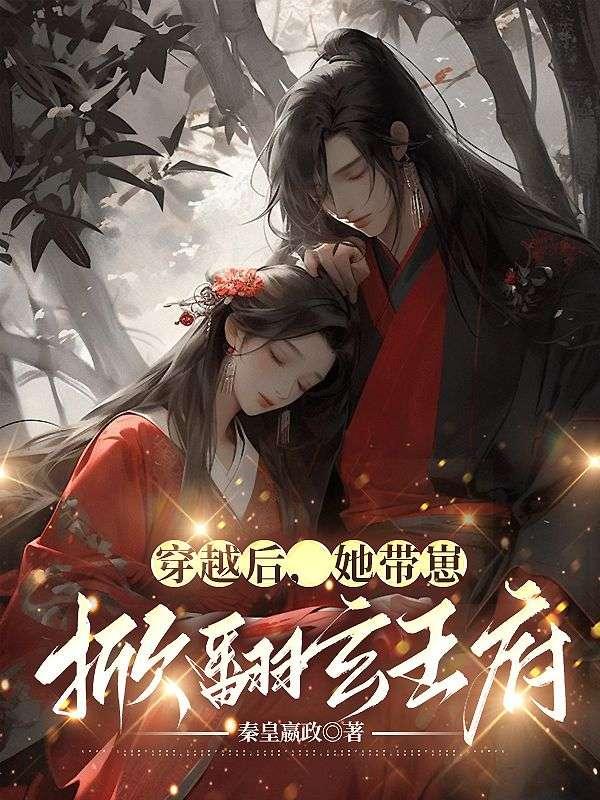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坐看仙倾 > 第404章 该叫日月换新天了(第1页)
第404章 该叫日月换新天了(第1页)
“方大人,匡诚和木菁这两人该如何处理?”
“道不同,只能让他们永远闭口。”
“可他们不过是凡俗之流,关在牢中谁也见不到,不会影响我们的大事。”
“青云天下有无数功亏一篑之事,都是死于。。。
雨落得极轻,却密如针脚,敲在茅草屋顶上,像无数人在远处低语。那株破土而出的嫩芽已被雨水打湿,却仍倔强地挺立着,叶片微微张开,仿佛要接住每一滴自天而降的讯息。
老妪坐在窗前,手中握着那支新来的柳笛,指尖一遍遍摩挲着笛身上的纹路。她知道这不是凡物??木纹里藏着星轨的痕迹,那是季忧年轻时在观微书院后山亲手种下的柳树所留。每一道年轮都记着一场春雪、一次离别、一段无人知晓的守望。
“你回来了?”她忽然开口,声音沙哑却平静,像是对风说,又像是对记忆讲。
屋内无人应答,只有炉火噼啪一声,溅出几点火星。可窗外的雨却忽然停了,檐角垂下的水珠凝在半空,晶莹剔透,宛如时间也被这无声的一问冻结。
片刻后,一只乌鸦从林间飞出,落在院中槐树枝头。它并未鸣叫,只是歪头看着屋里的人,眼中竟有几分人性般的悲悯。然后,它轻轻振翅,将一片湿漉漉的槐叶投进窗台。
老妪拾起叶子,见叶背浮现出一行小字:**“非归来,乃未走。”**
她笑了,眼角皱纹如藤蔓攀爬,却盛满了光。
“我就知道。”她说,“你从来不肯真正离开。”
她站起身,颤巍巍地走到灶前,重新热了一碗粥。这一次,她在碗边多放了一双筷子。
---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东海孤岛之上,一座由珊瑚与沉船残骸垒成的小庙静静矗立于浪尖。庙中无神像,唯有一盏琉璃灯长明不灭,灯芯是以九百九十九位医者临终前最后一口气吹燃,故称“愿心灯”。
此刻,灯焰忽地摇曳起来,映照出墙上斑驳的刻痕??那是历代前来朝圣者的留言:
>“我曾放弃一个垂死病人,今夜跪此赎罪。”
>
>“吾子因瘟疫夭折,然我已继承其志,行医三十州。”
>
>“我不信仙,但我信你教我的事:伸手比祈祷更有力。”
一名身穿灰袍的少年跪在灯前,双手捧着一本破旧医书。那是《季忧残卷?卷七》,全篇仅存三页半,字迹模糊,唯有一页末尾写着一句:“**病非天罚,乃是人间失温所致。治之以药,更须以心。**”
少年名叫陈知寒,是江南疫情中唯一幸存的孤儿。当年他化作石像前最后一眼,看见的是一个女子吹着柳笛走过街巷,笛声所至,冰雪消融。他醒来时已在鸣心堂,身边围满陌生人,人人手捧热汤,眼中含泪。
从此他发誓学医,哪怕资质平庸,也要走完那条未曾谋面的恩人走过的路。
“师父……”他低声呢喃,“今日又有三人痊愈。他们说,梦里听见了笛声。”
话音落下,灯焰猛地一跳,竟幻化出一道虚影??正是季忧的模样,草帽低垂,肩披旧蓑衣。他没有说话,只是缓缓抬起手,指向少年怀中的医书。
下一瞬,书页无风自动,翻至空白处。墨迹凭空浮现,逐字成句:
>**“若你愿做那盏灯,便不必问我是否还在。”**
>
>**“你看,他们已在唤你‘柳先生’。”**
少年浑身一震,抬头再看,灯焰已归平静,仿佛方才一切皆是幻觉。可那句话,却深深烙进了他的魂魄。
他伏地叩首,额头触地三下,然后起身,推开庙门,走入风雨之中。
身后,愿心灯依旧明亮,照亮了整片怒海。
---
数日后,西北荒原。
黄沙漫天,一支驼队艰难前行。领头的老者拄着一根柳枝为杖,背上背着一口锈迹斑斑的铜钟。钟上刻着七个字:“**听万人之声**”,据说是听涛馆初代馆主所铸,能引天地共鸣,唤醒沉睡良知。
老者名叫陆鸣远,曾是朝廷重臣,掌刑狱十余年,判案数千,从未错杀一人。但他始终记得自己年轻时曾因一纸奏章,导致三百流民被驱入绝境,最终冻饿而亡。
那一夜,他在梦中听见笛声,醒来后辞官远行,踏上赎罪之路。
如今他已七十有余,足迹遍布边陲,每逢灾厄之地,便敲响此钟。钟声一起,无论牧民、盗匪、戍卒,皆会驻足聆听,有人落泪,有人跪拜,也有人当场焚毁刀兵,发愿终生不再伤人。
“听说江南又起了旱灾?”随行少女问道。她是守夜坊弟子,名唤苏萤,因擅织“护心网”而闻名。那网以情丝为线,哀思为结,能在战乱或灾难中稳住人心,防止恐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