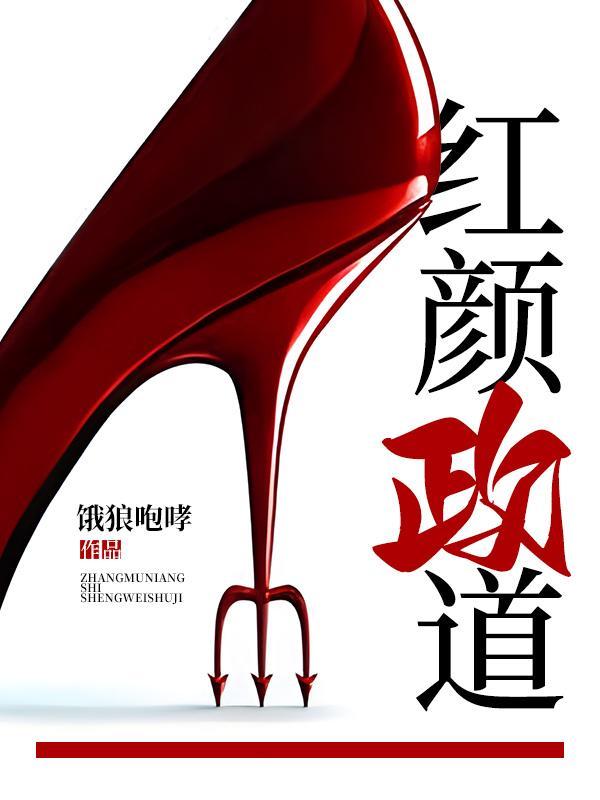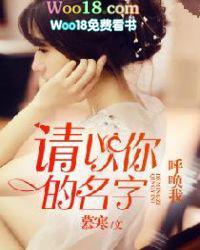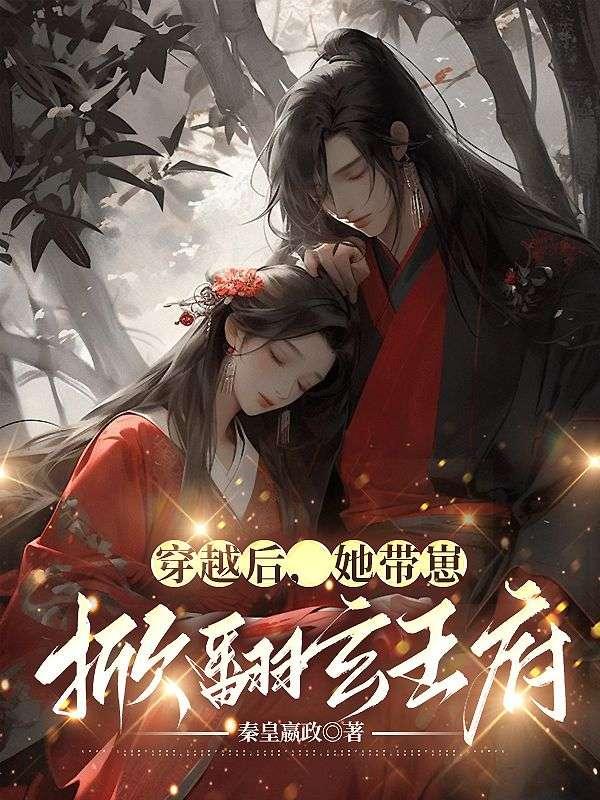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我的哥哥是高欢 > 第269章 乃是尔等离不开莫贺咄(第2页)
第269章 乃是尔等离不开莫贺咄(第2页)
刘黑闼双膝跪地,眼中含泪:“大人!我在恒州亲眼见过他们如何逼死佃户妻儿!他们囤粮不售,哄抬价格,害得百姓吃观音土活活胀死!我不甘心啊!”
高洋扶起他,声音低沉却坚定:“我也不甘心。可我们若用他们的手段去对抗他们,那我们和他们还有什么区别?你要相信我,只要给我时间,我会用律法、用制度、用民心,一点一点碾碎这些腐朽的根须。但现在,不是决战的时候。”
他下令释放族老,赔偿修缮祠堂费用,并亲笔写信向太原王氏、清河崔氏致歉。这一举动震惊朝野。有人讥讽他“向豪门低头”,也有人赞其“能屈能伸真丈夫”。唯有高澄冷笑不止:“二弟果然聪明,知道什么时候该扮菩萨,什么时候该扮阎罗。”
与此同时,恒州方面传来捷报:新政全面铺开,北原麦田扩至五百顷,预计秋收可达六万石;纸鸢学堂新增十二所,收容失怙儿童逾八百人;更有胡商主动请求加入官市贸易,愿以牛羊皮毛换取铁器书籍。薛孤延在信中写道:“百姓见您画像悬挂厅堂,晨昏焚香,呼为‘活菩萨’。若非军令在身,恐有人欲立生祠。”
高洋读罢,久久无言。他取出那朵干枯的野菊,轻轻吻了一下,放入怀中贴身收藏。
转眼清明将至,晋阳城外柳色初黄。高洋主持春耕大典,亲自执犁破土三丈,引来万人围观喝彩。就在此时,北方驿骑飞驰而来,带来惊人消息:阿史那云率三千突厥骑兵南下,途中遭西魏伏击,损兵八百,粮草尽失,现被困于雁门谷道,急需救援!
高洋当即召集诸将议事。多数人反对出兵:“突厥乃异族,素无信义,救之何益?且道路险峻,若中埋伏,恐损我主力。”唯有杜丰力劝:“不可不救!阿史那云曾助我退敌,若此时弃之不顾,今后谁还肯与我们结盟?民心、军心、盟心,皆系于此一举!”
高洋沉思良久,决然下令:“点兵五千,轻装疾进,我亲自带队!”高澄闻讯赶来阻拦:“你身为统帅,岂能轻涉险地?万一有失,晋阳危矣!”高洋看着兄长,平静地说:“正因为我是统帅,才必须去。将士们可以怀疑命令,但不能怀疑主帅的信义。你说对吗,兄长?”
四月朔日,高洋率军抵达雁门。天降大雨,山路泥泞,行军艰难。探马回报,李弼派出精锐万余,已在谷口设伏,只待突厥残部突围便一举歼灭。高洋却不急于进攻,反而下令全军扎营休整,杀牛犒士,大张旗鼓宣称“三日后决战”。
当夜,他亲率八百死士,攀崖绕道,趁着暴雨夜袭敌后粮仓,一把大火烧尽西魏积粟。次日清晨,李弼军心大乱,正欲撤退,高洋突然挥师强攻,与阿史那云内外夹击,大破敌军,斩首两千余级,俘获辎重无数。
战罢,高洋在谷中寻到受伤的阿史那云。她左臂中箭,脸色苍白,见到高洋时勉强一笑:“你果然来了。”高洋为她包扎伤口,轻声道:“我说过,只要有人愿意相信,我就不会辜负这份信任。”
回师途中,阿史那云策马并肩而行,望着远处青山叠翠,忽然问道:“你在恒州做的事,真的能在整个河北推行吗?”高洋望向南方,目光深远:“很难。世家盘根,官吏徇私,百姓麻木太久。但我相信,只要有一块土地开花,就会有第二块、第三块……终有一天,整个北地都会绿起来。”
五月十五,晋阳解严,恢复市贸。高洋奏请高欢,设立“民议司”,允许各县推选两名平民代表列席州政会议,参议赋税徭役。此举震动天下,儒林哗然,谓之“以下犯上,礼崩乐坏”。然民间欢呼雀跃,称之为“天子脚下开民智”。
高欢最终准奏,只加一句批语:“可行十年,视成效再定去留。”高洋知这是妥协之果,却已迈出关键一步。
某夜,月明星稀。高洋独坐书房,提笔撰写《晋阳新政纲要》。写至“凡官吏贪墨十两以上者,斩;纵容豪强欺民者,贬为庶人;阻挠义学建设者,流三千里”时,笔尖一顿,忽觉身后微响。
回头一看,竟是高澄立于门边,手中捧着一卷竹简。“二弟,”他语气复杂,“这是我整理的父亲早年军令汇编,里面有他当年镇压贪腐、整顿吏治的案例。或许……对你有用。”
高洋起身相迎,接过竹简,郑重道谢。兄弟二人对视片刻,终未多言,唯有烛光摇曳,映照出彼此眼中那一丝难以言说的微妙缓和。
窗外,春风拂过新栽的桃树,花瓣如雪飘落庭院。远处传来孩童诵读声:
“天地有情,苍生为本。
官不爱民,不如无官。
都督执笔,划破长夜,
一点星火,燃尽旧山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