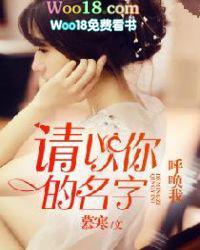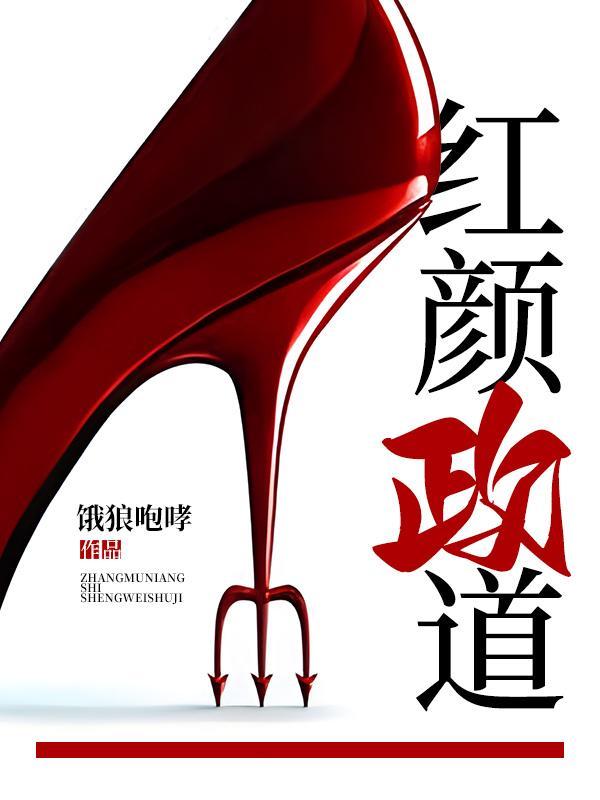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三国]穿着龙袍穿越了! > 第 62 章 第六十二章(第3页)
第 62 章 第六十二章(第3页)
不就是因这份招贤令想要去洛阳吗?何必说得这么弯弯绕绕的。
郭嘉答道:“那我可就真直说了?你欣赏陛下,是因他的仁厚之举,意在保全卢子干等人,我却是因为后面的那一句……”
陛下说:“天下贤才难求,朕知不可强求,令人共社稷之存亡。故而——”
……
“故而此番求贤,佐我仄陋,志在唯才是举,朕得而用之……”
刘备望着这最后一句,忽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你叹什么气啊!”同在此地的张燕着急地发问,“你还没回答我之前的问题呢!陛下与这招贤令一并发出的另一份公文
,是何意思?先别管那什么唯才是举还是唯什么是举了。”
一旁的张飞冷哼道:“你这么不客气,还找我大哥询问作甚?前几日还听你在夸耀你为陛下元从,于是受陛下气运影响,侥幸能将玉玺捧到陛下面前,那你有困惑直接问陛下不就好了?”
张燕理直气壮:“陛下每日为俗务烦忧,昨日又出城去了,我上哪儿去找陛下解惑?这不是看刘使君面善亲切,这才登门造访吗?”
张飞的脸色顿时和缓了不少:“……还算你这位张将军说了句人话。”
刘备无奈地笑着,打圆场道:“好了,这点事情也值得争执吗?我不过是在想,陛下这句唯才是举,请天下有志之士入京相助,到底能引发多少波澜。”
这完全是一句颠覆过往选人选官规矩的话,说出在此刻,不亚于石破天惊。
对于刘备这个忽然就因陛下的缘故得到了太守官职,又忽然得到机会匡扶汉室、助力陛下回京的人来说,更是感触颇深,心头震荡。
察举制下,被列入候选的官员光只是有才,还远远不够,还需要有乡里闻名的孝亲忠君的名声,有能和州郡官员往来的门路,才有那么一线的希望成为“孝廉”,进而有为官的资格。
但对于陛下来说,这祖宗之法却是不必非要遵从,也确实不能遵从的东西。只有这一句“唯才是举”!
刘备向张燕看来,眼中不无羡慕之色:“张将军不能体会到,陛下有此一句吗?若是拘束于祖宗之法,先令州郡官员察举孝廉,举荐到洛阳,再令他们通过考核,选调上任,已不知过去数月了,还谈什么走在董卓的前面。就似早前,若非要等到何进大将军的部将来援,而非黑山军鼎力相助,陛下恐怕早已为董卓所害。这唯才是举,实是因亲身体验而来啊。”
张燕一怔,脑中竟又短暂地飘过了彼时陛下和吕布的那句话,便是那句“他不是我的忠臣良将”……
又听刘备说道:“我先前唏嘘,是怕陛下这一句唯才是举,让士人觉得陛下不在乎德行,麾下的官员势必一团乌烟瘴气,能成什么事?虽有寒门黔首闻声来投,却也难免让陛下招来非议,不知是好是坏。”
张燕也急了:“那……”
“不,张将军不必忧心。”刘备宽慰道,“若是将这招贤令的前后连贯起来,仔细通读,又怎会有这样的疑问呢?愿不顾钱财田地赏赐,以身报国者,必是忠贞之人。欣赏陛下巧救百官,威逼董卓者,必是仁厚孝义之士。这句唯才是举,更似陛下给家世不显者,额外提供一条应邀而来的门路,并非真在说,只要会些文墨,便能来此谋求高就。”
张燕闻言,微不可见地松了口气。
刘备问道:“那么张将军应该不难理解,为何在这招贤令后,竟然还有第二份天子诏令,叫做劝学书了吧?”
张燕忐忑地发问:“……还是因为黑山军?”
他的重要性有这么大吗?这弄得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刘备却是郑重地点了点头:“仗义之人,不分是否宰猪杀羊,流窜山野,是否结识高门,家财万贯,这便是陛下在那招贤令上表示的态度。但黑山军中,连识字者都寥寥可数,陛下又要如何力排众议,让你等接管要职呢?天下能人群聚洛阳之时,你等也当早日学有所成呐。”
张燕抓了抓头发,低头看向了手中的劝学书,压下了眼眶里一闪而过的热意与动容:“可我真不是读书识字的料,这事你们都知道。”
他或许对于局势变化还算敏锐,也知道自己该如何做,才能受益,但真到了读书识字这事情上,他就真是两眼一黑了。
“所以陛下在这劝学书中,不是引用了荀子的话吗,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便是从二三字开始,也总好过从未行动。”
刘备努力忽略掉了一件事,就是他早年间在卢植麾下读书的时候,其实也没太好好读,并不能算是个好学生,但这并不妨碍他在意识到了陛下的想法后,向眼前这位同僚传达圣意。
何况,张燕有时候说话是冒犯了一些,却也不失仗义,是个值得一交的朋友。
“还有,陛下不是也给出了解决方案吗?袁氏有心捐献典籍,用于填补洛阳在大火过后的损失,蔡夫人也正在修复熹平石经,并将其余典籍默背抄录下来。可这场火中烧毁的,何止是那些名家名篇呢,还有诸如《急就篇》之类的识字读本,也该重新复原,以石刻的方式保存下来,避免再遭劫难。军中士卒当从此开始,知汉字,识道义,明礼教,与那大肆劫掠的西凉军区分开来。”
“这既是给了张将军一条门路,又何尝不是在为洛阳幸存的百姓指一条特殊的生路,也给他们一份信心呢?”
“……”
刘备:“张将军?”
张燕踉跄着后退了一步:“……我,我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