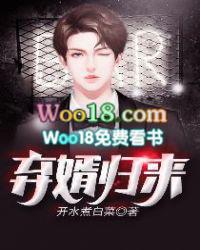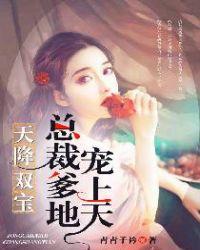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大唐协律郎 > 0263 举目仰望如见北斗(第1页)
0263 举目仰望如见北斗(第1页)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里,裴?先一直都待在州府内查阅源复入州以来凡所颁行的政令,以及州府下属诸曹相关的文书。
他一直都在斥责源复秉性风格远逊其父,这其实也是稍失公允的。源复倒也不是全无遗传,起码在州府。。。
源复接过那名帖,脸色顿时一白,双手不自觉地颤抖了一下。他抬头望了一眼仍在碑林中巡视的武惠先与张岱一行人,心中顿时咯噔一下。
“这……这是河南黜陟使?!”他喃喃自语,随即猛地转身对身旁的属官低声喝道:“立刻派人去州府布置!所有案卷、账册都要重新整理一遍,凡有出入之处,速行更正!再命人将州衙前前后后打扫干净,务必整洁肃然,不得有丝毫疏漏!”
那属官连忙应诺而去,源复却仍站在原地,眉头紧锁,心乱如麻。
他当然知道武惠先是谁。
此人乃当朝重臣,出身清贵,素以刚直不阿著称,曾于数年前巡按江南,一举罢免十余州贪吏,震慑一方。如今被任命为河南黜陟使,来意显然非同小可。
而自己在汴州这一年的所作所为,虽不敢说是罪大恶极,但也绝非无可指摘。尤其是近月以来,为了应对朝廷追查张说封禅之事的影响,他在州内横征暴敛、设卡抽税,甚至纵容属下盘剥商旅,种种劣迹,早已传得沸沸扬扬。
若武惠先此番前来,真要彻查一番,恐怕自己这刺史之位,怕是坐不稳了。
想到这里,他不禁回头望向那正在碑林间缓缓前行的几人影子,心中一阵发寒。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名差役气喘吁吁地跑了过来,跪地禀报:“大人,州府外已备好仪仗,只等您亲自出迎。”
源复点了点头,强压下心中的不安,整了整衣冠,快步走出相国寺,翻身上马,率领一众属官和仪仗队,浩浩荡荡地往州府方向赶去。
一路之上,他不断思索对策,脑海中闪过无数念头:是否该先行拜访武惠先,试探其口风?还是索性装作不知情,静观其变?
但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两个想法。
前者太过主动,反而显得心虚;后者则太过被动,万一武惠先已经掌握实情,那自己连最后的机会都没有了。
他只能走一步看一步,尽量拖延时间,同时做好最坏打算??若是真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或许只能上表请辞,保全自身,甚至谋求一个调任边地的出路。
……
与此同时,相国寺碑林之中,武惠先正缓步穿行于石碑之间,神情冷峻。
张岱跟在其后,目光扫过一块块刻满文字的石碑,嘴角微扬,似乎颇为得意。
“裴公果然慧眼如炬。”他轻声道,“这些碑文,字字句句皆是百姓所立,记录的都是州官善政。可惜啊,如今汴州之政,却是与这些功德碑格格不入。”
武惠先没有回应,只是停下脚步,伸手抚过一块斑驳的碑面,神色复杂。
“此碑,是开元十五年所立。”他缓缓开口,“当时汴州水患初平,前任刺史率民筑堤,赈济灾民,百姓感念,自发立碑于此。”
顿了顿,他又道:“如今不过短短三年,汴州竟已成此般模样,令人唏嘘。”
张岱微微一笑:“世事无常,人心亦难测。”
武惠先终于转头看向他,目光锐利:“你此番前来,究竟是为何而来?”
张岱笑容未减:“自然是为义造织坊一事,兼受宣抚使文书,巡查州县民生。”
“仅此而已?”武惠先语气略沉。
张岱轻轻摇头:“自然还有别的。”
他顿了顿,低声道:“裴公可知,此次朝廷遣使,并非仅仅是为了调查汴州一地之事。而是因张说封禅之举,已然引发朝野震动,陛下震怒之下,欲借黜陟之机,整肃河南河北诸州官吏。”
武惠先闻言,眼中闪过一丝异色。
张岱继续道:“而我之所以同行,是因为……有人希望我能亲眼见证这一切。”
“谁?”武惠先问。
张岱笑了笑,却没有回答。
两人沉默片刻,武惠先忽然道:“那你认为,源复当如何处置?”
张岱沉吟片刻,道:“若他是真心为民,即便手段粗暴,尚可宽容;若他是为己私利,那就该严惩不贷。”
武惠先点头:“我会秉公而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