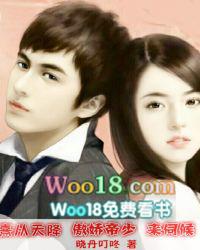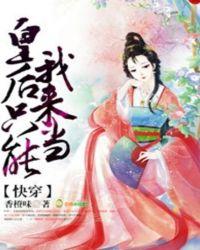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四合院之饮食男女 > 第112章 吉祥物(第3页)
第112章 吉祥物(第3页)
课后,陈伯找到王亚娟,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是他亲手写的字:
“我一直觉得,自己老了,话说不清,耳朵也不灵,是个累赘。可现在我发现,只要我想说,总有人愿意听。甚至,我还可以说给别人听。”
王亚娟握紧那张纸,一句话也说不出。
五月的第一个周末,社区迎来一年一度的“共享午餐节”。不同于往年各家端菜拼桌的形式,今年主题定为“味道的记忆”??每位参与者需带来一道承载家庭故事的菜肴,并附上简短讲述。
那天阳光明媚,三十张饭桌再度摆满天井。有孩子带来母亲祖传的酱萝卜,说那是爸爸化疗期间唯一肯吃的东西;有老人端出一碗素馅饺子,哽咽着回忆亡妻生前最爱包这款馅;刘红梅则拿出一锅秘制红糖糍粑,笑着说:“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食谱,她说,甜食能治心病。”
轮到赵建国时,他默默放下一碗清汤面,上面卧着一个荷包蛋。
“没什么特别的故事。”他说,“就是每天早上给自己煮的。坚持了四十多年。以前一个人吃,现在……偶尔也有人一起。”
话音落下,好几个年轻人立刻起身,跑去厨房盛面,回来坐下,一声不吭地陪他吃完。
这一幕被小陈悄悄拍下,后来成了纪录片《无声之力》的开场镜头。
夏天来临前,市电视台举办“最美社区工作者”评选,提名名单中赫然出现王亚娟的名字。消息传来时,她正在指导苏晴调试新开发的“长者守护手环”??一种可监测心率、跌倒报警并一键呼叫邻居的智能设备。
“我不参选。”她果断拒绝媒体采访请求。
“为什么?”记者不解,“您做的事值得被看见。”
“因为我不是一个人在做。”她平静地说,“如果非要选,该选赵建国、刘红梅、李晓芸、小陈,还有那些从没上过新闻的普通人。他们才是这个院子的心跳。”
最终,奖项颁给了“37号院全体居民”。
颁奖词写道:“他们证明了,真正的文明不在于高楼有多高,而在于低头时能否看见身边人的鞋是否湿了。”
秋天的一个黄昏,王亚娟收到一封信,寄自国外。拆开一看,是那个曾涂鸦拼音的孩子寄来的。他已经硕士毕业,正在攻读社会学博士,研究课题正是“中国城市老旧社区的情感治理模式”。
信末附着一句话:“老师,我现在懂了,当年您埋下的那只铁盒,装的不是记忆,而是种子。”
她将信仔细折好,放入抽屉最深处。窗外,夕阳染红了整片天空,海棠叶沙沙作响,像在低语。
冬天再次降临,第一场雪落下时,新的“时光胶囊”仪式如期举行。这一次,每位居民都被邀请写下对未来十年的寄语,封存在复刻的铁盒中,将于2034年冬至开启。
王亚娟写的仍是那句话:
“愿你们仍有勇气争吵,仍有耐心倾听,仍能在平凡日子里,为彼此点亮一盏灯。”
仪式结束当晚,微信群里突然跳出一条新消息:
【匿名发布】
“我想谢谢那个在我失业时偷偷塞给我一袋米的人。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我活过来了。”
不到十分钟,回复刷屏:
“是我。”
“也是我。”
“还有我。”
最后,王亚娟轻轻回了一句:
“我们都曾是那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