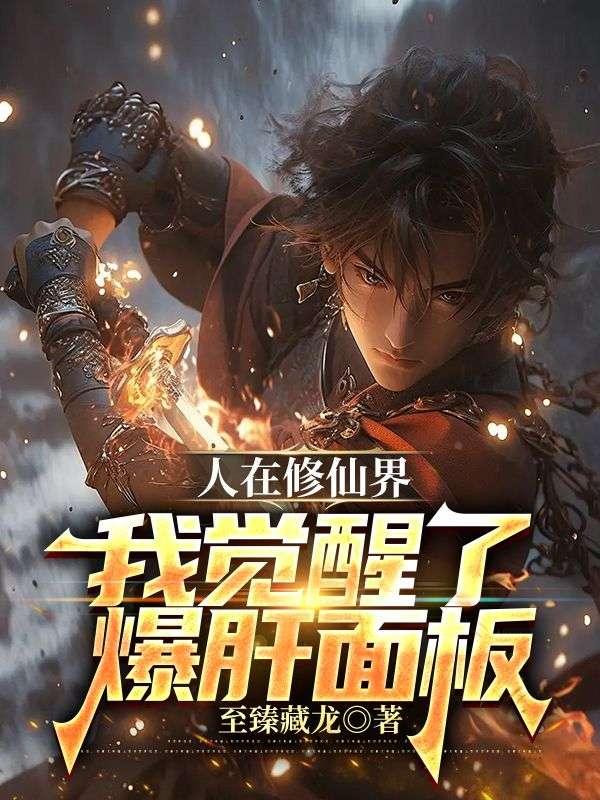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哥布林重度依赖 > 第335章 谨慎补刀与轻松治疗(第2页)
第335章 谨慎补刀与轻松治疗(第2页)
三天后,我们启程。
随行的还有三位年轻人??曾在学堂听我讲课的学生,听说我要再出发,执意同行。一个是精灵混血儿,擅长用树叶记录声音;一个是失语的矮人少年,靠手势和壁画表达思想;最后一个,竟是当年那只雪狐的后代,如今已能口吐人言,自称“听风者”。
我们组成一支奇特的队伍,在风雪中缓缓北行。沿途,我们不再依赖地图,而是依靠“共鸣”前行??每当夜深人静,小女孩便会摊开那张羊皮纸,轻声念出一句古老咒语般的短语:“我记得,故我在。”
每一次念诵,地图上的某条路线就会微微发亮,像是被某种深层记忆唤醒。有时我们会走进一片看似荒芜的山谷,却发现岩壁上布满了天然形成的刻痕,拼凑起来竟是一首完整的叙事长诗;有时一场暴风雪过后,积雪自动排列成箭头,指向下一个方向。
第十日,我们抵达“回声湖”。
湖面如镜,覆盖着半透明的冰晶,倒映着天空却不见我们的影子。唯有当我开口说话,湖底才会泛起涟漪,并从中传出另一个声音,一字不差地重复我说的话??但语调不同,带着悲伤、愤怒、喜悦或疑惑,仿佛是无数个“我”在不同时空的回应。
“这是‘自我之渊’。”听风者低声解释,“传说中,每个叙述者都必须在此面对自己未曾说出的部分。”
我走近湖边,试探着问:“如果我不记得过去,还能算是我吗?”
湖水震荡,数十个声音同时响起:
“你是你写下的名字。”
“你是别人眼中的影子。”
“你是空白页上的第一道划痕。”
“你是拒绝盖棺定论的亡魂。”
“你是不肯闭嘴的死者。”
“你是不敢醒来的人。”
“你是唯一诚实的骗子。”
最后,一个极轻的声音浮现:“你是那个……本可以什么都不做的普通人。”
我跪倒在冰面上,泪水滑落。
原来我一直逃避的,并非记忆的缺失,而是责任的重量。我曾以为放下笔就是解脱,可实际上,我只是把重担交给了别人。而现在,这些人正跟着我走向未知,因为他们相信??我仍知道些什么。
那一夜,我在湖畔写下一封信,封好后投入冰缝:
>致所有读过我故事的人:
>我不是一个英雄,也不值得被纪念。
>如果我的文字曾让你感到一丝温暖,请把它传递出去。
>如果你觉得某个情节虚假,请大胆改写它。
>如果你觉得自己从未被讲述,请拿起笔,为自己命名。
>故事不属于作者,正如河流不属于源头。
>它们只是经过我们,然后奔向更远的地方。
>??一个仍在学习倾听的人
第七天,我们登上“断章岭”。
这里没有树木,只有无数断裂的石碑矗立在风中,每一块都刻着半截句子、残缺的名字、中断的誓言。有些碑文我能认出,是我在旅途中遗失的手稿片段;有些则全然陌生,像是来自尚未诞生的篇章。
我们在山顶扎营。当晚,小女孩做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