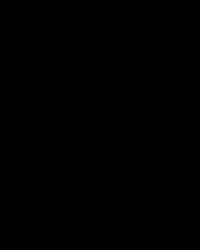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我与太子举案齐眉 > 4050(第18页)
4050(第18页)
池子里养了一池锦鲤,她便盯着它们游弋其中,金色的尾部在水面荡起了浅浅涟漪。
她凝眉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先与我说道说道,我心里也有个底……”
“令狐尉定是把这张陈条藏在了哪,只要找到陈条,便可揪出幕后之人。”陆昆明越说越有些激动,眼眶也湿润起来。
两人甫一落座,便见远处传来一声喧哗,两人循声望了过去,见穿着一身赤红团花袄,头簪?髻的女子被人簇拥着,一众贵女们都朝她福下身子道,“参见殿下。”
容妈妈趁机又说了她一回,这才得意地踅了出去。
妤娘在家时偶尔也会办起诗社或是赏花宴,邀那些手帕交的姐妹上家来相聚,她当然也见过那样明媚的场景。
他冥思苦想,一时不知自己错在了哪里,李照广凭借李贵妃的宠信而上位,可他本人锋芒太甚,并非藏得住心性之人,既然案件移交大理寺,他不信他还能毫无动作,况且令狐尉身上还有他的把柄。
容妈妈听到动静忙迎了出来,将明蕴之引到净室沐浴去了。
“嗯。”他拥着她躺下来。
“你问这个做什么?”
原本京令已捕到真凶,案件也暂时偃旗息鼓,可没想到,数月之后,又开始接到男童失踪的报案,而后续的发展,与年前的案件如出一辙。
“世子还在书房没出来,好像在琢磨案子呢,世子妃也快去劝劝吧。”
话虽如此,心里却不禁遗憾,两个截然不同的人,连说话都说不到一块,日子久了,当真还能保持如今这般平和?
还没踏入静思堂,她的手也不知何时便松开了,他瞥了一眼,默默叹息。
这桩男童失踪案,她此前也听说过一些,实在是太残忍、太离奇,从而引起人心惶惶。
明蕴之靠在他身上,小口小口地喝完一整碗醒酒汤,这才对他说,“其实我酒量也没那么差,是我没想到到这个青梅子酒那么烈……”
她本能地摇头,忽地又想起自己的身份,于是凝滞了一下道,“弹过一些,弹得不好,实在是好久没弹了……指法都生疏了……”
宋心钰点头,“妤娘,我也很高兴认识你,下回我定是要到你们府里玩的。”
明雪在她点头后,眉梢立即浮起一抹喜色,嘴皮子噼里啪啦蹦出了一串,“听闻小公爷谢宣长相俊美,风度翩翩,今年将将及冠,尚未婚配,国公夫人为此操碎了心,想来这次办起茶会,实则是暗中相看起未来的儿媳妇呢。”
明蕴之叹息一声,容妈妈不愧是跟在曾夫人身侧多年的老奴,两人的嘴脸如出一辙。
有她这个定海神针,到了吃饭时,父子俩也各退一步,维持着一种诡异的融洽。
明蕴之一听她这么说,心里也有了个大概,账房管事可是油水多的位子,怪不得容妈妈到了王府,这新裁的衣裳可是越来越多,腰膀子也越来越圆了。
明蕴之惶恐,朝她比了个噤声的手势,“慎言。”
所以,他与令狐尉认识的时间,可能比大家想得还要早。
她摘下食指上的松花石戒指,塞入明蕴之手心里,“这只戒指就送给你,当我们的见面礼吧。”
想到此处,她转头又吩咐绮萝,“你近来多留意打听一下容妈妈和谁亲近,和谁积怨,注意别打草惊蛇。”
罢了,多思无益,他闭上眼,一夜无梦。
“行。”宋心钰大方接过,将香囊系在自己腰上。
从现有的资料看,他是陶坞人,父母早亡,亲戚疏离,所以早早便入了观。
她脑里还乱成一团浆糊,回过神时,才发现他已掩上房门离去。
这话说得张屿脸上微讪,不禁开口,“你才高行洁,不过是因你家世好,我无权无势,自然不愿开罪那人,明哲保身,难道有错吗??”
绮萝醒过神来,忙搁下盆子,抽出手绢替她擦拭,一面擦一面道歉,“对不起,容妈妈,要不您脱下来,我给您拿去洗洗吧。”
明蕴之心头冷笑,脸上却做出抽抽搭搭的姿态来,一抽一泣道,“容妈妈好没道理,我在屋里睡得好好的,你冷不防地到我面前来,二话不说就扣了我一脸屎盆子,敢问我做了什么,何以当得你左一句不知廉耻,右一句狐妖媚子?”
明蕴之心情并未受到影响,接过那条软璎珞,对着镜子比对起来,一颗颗指甲盖大小的珍珠串成的链子,吊坠则是元宝状的红宝石,样式简约,却很有质感。
只是在儿媳面前挨训,睿王脸色也讪讪的,支吾道,“母亲给儿子留点脸面吧。”
宋心钰见旁边的明雪脸色越来越苍白,简直要成了一张白纸,于是更加起了恶作剧之心。
听到人头,明蕴之的心跳在刹那间也冒到了嗓子眼,她只是个替嫁的假世子妃,难道连命也要兜进去?那显然不大值当。
说完,又唤了个小丫鬟给她们上茶,这才踅了出去。
侍从们连忙把裴玄朗扶起,抬到轮椅上,发现只是擦破了一点皮,才都松了一口气,小心翼翼道:“您消消气。”
他们看不清山间小筑里的情景,也不敢看,此刻个个摸不着头脑,二少奶奶和崔夫人到底做了什么,惹二公子如此气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