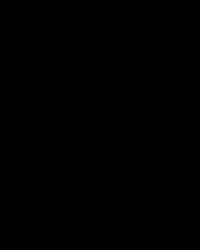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豪商·女强 > 140150(第9页)
140150(第9页)
“明月?!”那僧侣尚未回答,童琪英的声音就自斜前方响起。
他裹得棉球也似,鼻尖和下巴冻得红彤彤的,笑容径直从眼底涌出来,又惊又喜,“天这样冷,你真的来啦!”
他身后还跟着两个眼熟的随从,手里各提着一只陶罐,也不知装了什么。
“商人无信不立,”明月笑着同他见礼,“既然说了,自然要来。”
“明月,我,”童琪英骤然回神,带着点忐忑和期冀地望着她,“我可以这样叫你么?”
江老板,江老板,太生疏了。
她既来了,绝非对自己无情,称呼亲昵一点,也无不可……吧?
明月挑眉,“可不可以的,不都叫了么?”
谁说只有自己在试探呢?
见她并未着恼,童琪英感到由衷的快乐,“瞧我,竟在外面说话,天冷,快进屋吧。”
“你从哪里来?”明月边打量屋子边好奇道。
众济寺到底有没有钱另当别论,别院的装潢十分朴素,只是简单的砖墙盖瓦,屋子里面也清清静静的,唯有墙上挂了一轴山水,与周围的土炕、素被、木桌格格不入,估摸着是童琪英自己带来的。
“南方少有这样的好雪,快坐。”进了屋,童琪英解下斗篷,早有小厮端了热水来洗手,又有热茶,“我去后山取了松枝上的雪,正好你来,煮一壶茶你喝。”
明月也洗了手,围着炉子烘去身上寒意,闻言笑道:“一小盏尝个味儿就好,免得我不识货,糟践了好东西。”
她本不大在意喝什么。
况且雪水性寒,女子不宜多饮。
“甚么好东西,只占了点清冽的便宜,又有些松香罢了。”童琪英也笑了,坦然自嘲道,“不过是我百无聊赖,附庸风雅而已。”
这时节来别院的也多是高门,其中不乏与童家有旧的,真是哪里都躲不开。作为晚辈,童琪英少不得亲去拜会,可他也实在不愿日日寒暄,索性借口多出去,眼不见为净。
“随便坐吧,这里讲究不得,委屈你了。”他说。
“这里虽素净些,可该有的都有,炕头烧得热乎乎的,墙瓦亦不漏风,童相公尚且住得,我何苦之有?”明月跟着笑,去窗边小桌坐下,看他烹茶。
童琪英的双手细长白皙,骨节分明,一看就是没做过粗活的公子哥儿出身,又自小浸染,凡与琴棋书画诗酒茶之流相关的消遣,做起来总是很赏心悦目。
明月托腮看着,毫不避讳,倒把童琪英看得不好意思,脸蛋红扑扑的,手下一抖,几滴茶水溅了出来。
明月莞尔,侧过脸,透过窗缝看院景。
很常见的小两进院子,角落里长着一棵歪脖子松树,松针上堆满白雪,倒有些意思。
“好端端的,怎么到这里来?”明月转回视线,像是玩笑,又带着几分认真地说:“该不会是因为我吧?”
童琪英的动作顿了顿。
他沉默片刻,终于低低地笑起来。
果然还是她,直白坦率,又有几分近乎天真的残忍,从不掩饰。
明月的意思很明显,有童老头儿的前车之鉴在,童家其他人的态度和立场可想而知,若童琪英真的因为她跟族人闹翻,童家人定然恼火。他们不可能放弃自家前途无量的晚辈,那么就势必要把怨恨倾泻到她身上。
更有甚者,为了劝童琪英“迷途知返”,说不定也会有童家人想方设法地叫他吃些苦头。
比如眼下,童琪英究竟是自愿、主动过来的,还是被逼过来的,这一点对明月很重要。
如果是后者,说明童琪英的处境已经非常尴尬、危险。
明月从不认为虚无缥缈的情爱能够支撑漫长的人生。
也许现在童琪英真的很喜欢她,自觉有情饮水饱,抑或在家人的反对下倔劲儿上涌,但终有一日他会厌倦、会后悔,会觉得当下的窘迫和困顿全是由明月这个外人造成的……
明月是个商人,她固然看好童琪英,希望眼下漫长的押宝能在未来的某一日得到丰厚的回报,但如果局面提前失控,她就必须重新权衡:
尚未完全成功的官场伙伴可能带来的利润能否覆盖若干现任官员敌对的风险?
如果不能,现在放弃童琪英,童家人会相信她、放过她吗?
如果能,那么她需要调动怎样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才能确保对方在回到正轨后回馈给她更为丰厚的回报?
“不,”茶水重新开始流动,伴着清脆的落水声,童琪英干脆利落道,“归根究底,是为了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