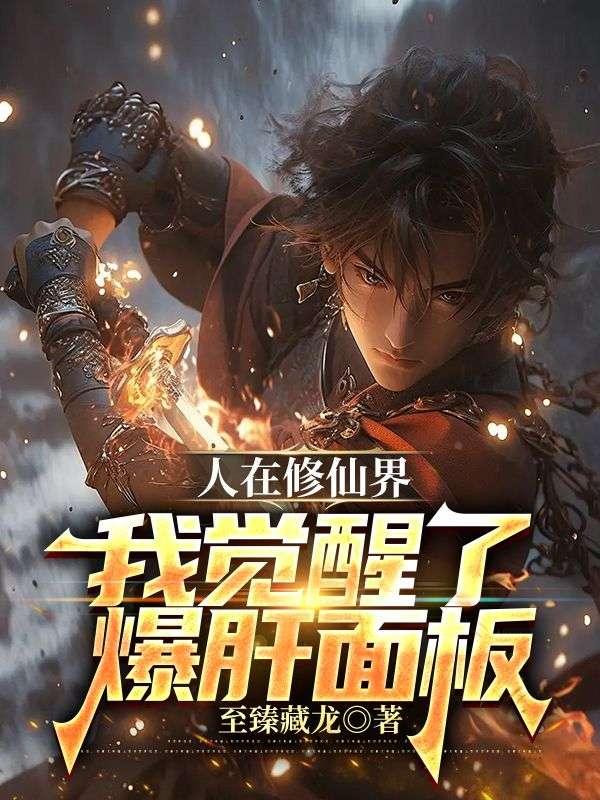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当反派雄虫被剧透 > 3040(第18页)
3040(第18页)
到底生了什么病啊,会不会很严重啊……!!
(咬牙切齿地蹦下床)
在外面病着算了,不是身体很好,对自己很了解吗。
不要想让我陪你去医院,住院我也不会去看你的!
(围着床绕来绕去)
对,医药费也不管!
生不生病和我有什么关系。”
说完摔到床上,卷起被子,陷入安静。
在克莱德快要睡着的时候,隔壁又突然从床上坐起来诈尸,愤愤道,“哼,谁惜得管你!”
“……给兰易斯多发点零花钱?算了还是把这小子光脑拿过来保险。”
接着又披着被子在屋里骂骂咧咧了一圈,这次语气明显弱了很多,似乎在确认什么般,委屈又小心,“真的不要我了啊……”
“不要就不要,谁稀罕!”
惊醒的克莱德:……
更可怕地是隔壁的诈尸循环总会以一句叹号开始,从愤怒到委屈无缝切换。
克莱德连人带脑袋都缩到了被子里,被吵得一晚上没睡好,天快亮了才好不容易眯了一会,就硬生生被敲醒了,和黑眼圈更严重的法斯特大眼瞪小眼。
*
不知道曼斯菲尔德检查的是什么,半晌没有出来。
没休息好的两小只坐在楼梯上,目光呆滞地望向诊室,怕自己睡过去,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大概复述了遍失败的约会实况。
“原来昨天没有吵起来啊,怪不得……”克莱德语气有些遗憾。
雄虫懒洋洋地靠在自己身边,不愿动弹,克莱德只好调整姿势,让兰易斯靠得舒服一点,肌肤的热度透过衣料传了过来。
鼻尖也若有若无萦绕着一股淡淡地甜味,引得倦意和疲惫一点点涌了上来。
“嗯。为什么要吵起来?雌父和雄父从没有吵过架。”
兰易斯杵着下巴避免脑袋垂下去,衣服坏掉的肩膀紧紧贴着克莱德,生怕坏事被人发现。平淡的声音里藏了些许懊恼,后脑的呆毛丧丧地耷拉着。
“雄父说要不是我突然敲门进去,雌父要被哄好了。”
““哄~好?””克莱德轻笑了一声,似乎是因为困倦,雌虫大半个身子靠在墙面上,说话不自觉有些慢,尾音如往常般微微扬起。
不知道是不是兰易斯的错觉,和往常的温柔不同,带了一点嘲弄的意味。
“从没有吵过架,感情真好啊。”他拨了拨兰易斯的小卷发,好奇似问道,“您是曼斯菲尔德阁下的幼子,有没有发现曼斯菲尔德阁下对你们和法斯特阁下的态度有些不同?”
“非常不一样。”兰易斯怨念满满,对此相当有发言权,差点就从克莱德身上跳了起来,想起穿坏人家的衣服,又默默贴了回去,掰着手指告状。
“对我们就条条框框,这不行那不行!犯错还要受惩罚。”
“对雄父特别好说话,言听计从,没有底线。”
偏心,赤裸裸的偏心!
曼斯菲尔德是有点强迫症在身上的,总会把莫名其妙的育儿守则奉为圭臬。
哥三个犯了错,他就是铁面无私的公正老父亲,三只幼崽一起抱胳膊抱大腿撒娇卖萌都不好使,只能抓耳挠腮引经据典地和雌父讲道理,再被一条条无情地反驳回来。
法斯特就不一样了,他无论编出什么离谱的理由,曼斯菲尔德都只会卡顿一会,思考片刻后神色如常地表示,“嗯,你说的对。”
——雌父的思考时间视法斯特理由的离谱程度而订。
克莱德感觉袖子都快被紧紧贴着的兰易斯蹭掉了,不自在地向后仰了样,学着兰易斯的模样,单手托腮轻轻重复了一遍,“言听计从,没有底线。”
“我想,这就是问题所在。”
面对亲密无间的爱人,本该是情感最自在放松的时候。
而曼斯菲尔德却恰恰相反,在外面如鱼得水,在法斯特面前却紧绷呆滞的像一块木头,不敢泄露丝毫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