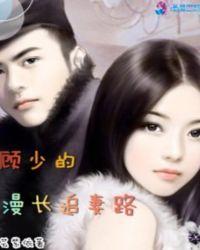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为变法,我视死如归 > 第244章 王家一门双圣(第2页)
第244章 王家一门双圣(第2页)
赵顼凝视天际良久,轻问:“此声若传至辽境,他们会作何想?”
“要么退避三舍,要么倾巢而出。”王小仙缓缓道,“但无论哪种选择,我们都已准备好了。”
果然,半月之后,辽国南院大王耶律仁先紧急召回萧禧,取消一切对宋施压行动。细作密报,辽廷内部激烈争论数日,最终达成共识:暂不对宋用兵,转而加强对女真诸部的控制,以防后院起火。更有消息指出,耶律仁先曾对着地图喃喃自语:“宋有王小仙,犹如卧榻之侧藏猛虎,不可轻动。”
九月初九重阳节,王小仙奉旨巡视西北边防。他率三百骑自长安出发,沿途视察屯田、校阅士卒、慰问归附的党项部落。每到一处,皆亲自教授农耕技术,讲解《千字文》与《论语》节选。一名年逾六旬的老酋长拉着他的手泣不成声:“我家三代牧羊,从未想过子孙能读书识字。如今孩子们不仅能写名字,还会背诗了!”
返程途中,他在绥州接到急报:辽国派出一支“使团”,名义上是来贺冬至,实则携带大量金银珠宝,试图收买宋军边将,策动叛乱。为首使者竟是当年被贬的旧党官员韩缜之弟韩纬,此人早年因贪腐罢官,近年流落塞外,竟投靠辽国。
王小仙当即下令:“不动声色,放他们入境。沿途驿站加倍供应饮食,让他们以为阴谋得逞。待其抵达太原,再一举擒获。”
十月初五,韩纬一行进入代州境内。他们不知,早在其入境之初,霹雳营便已化装成商旅尾随跟踪。当夜宿于雁门关外客栈,正密会两名伪装成守将副官的宋军细作时,数十名黑衣武士破门而入,瞬间将其党羽尽数制服。搜查行李,发现账册一本,记录了拟贿赂的将领名单、金额及接头暗语,其中竟包括枢密院某位副使。
此案震动朝野。赵顼震怒之下,连罢三名高级武官,重新整顿边防人事。王小仙借此机会,推荐李承恩兼任河东安抚使,全面接管沿边军政事务,并推行“军功授田制”??凡击退外敌、抓获奸细者,不论出身,皆可获得屯田土地与免税优待。
冬至前夕,王小仙再次入宫觐见。赵顼赐坐,关切问道:“卿常年奔波,面色憔悴,何不多休养几日?”
王小仙微笑道:“臣身体尚可。倒是有一事萦绕心头,迟迟未决。”
“但说无妨。”
“陛下可知,为何我坚持要在兰州建火器研究院?”他顿了顿,“并非只为造炮制枪。臣真正想做的,是让党项、吐蕃、回鹘的年轻人学会炼铁、铸铜、测算距离、绘制地图。这些技艺本属华夏正统,却被视为奇技淫巧,久遭轻视。可若我们自己不用,敌人就会拿来对付我们。不如主动传授,化敌为友,共御外侮。”
赵顼动容:“此乃长远之计啊……卿所虑者远胜庙堂诸公。”
王小仙起身拱手:“臣斗胆请旨:自明年起,每年选派百名少数民族青年赴兰州学习,费用由朝廷承担。学成者不仅可任火器监技师,还可返乡兴办工坊,带动一方民生。”
赵顼当即允诺,并下诏设立“西学专项银”,岁拨五万贯。
腊月廿三,小年之夜。汴京飘起今冬第一场雪。王小仙独坐书房,翻阅各地奏报。江南白糖产量突破百万斤,百姓婚嫁皆以“王公糖”为聘礼;蜀中井盐改良工艺,成本降低三成;就连最偏远的邕州蛮区,也开始种植从西北引进的耐旱麦种。
他合上卷宗,抬头望向窗外。雪花无声落下,覆盖了整座城市。忽然,一阵急促脚步声打破宁静??宋玉冒雪而来,手中紧握一封密信。
“相公!”他喘息未定,“兰州急报:第三尊震天炮试射时发生膛炸,三名工匠当场身亡,十余人重伤!”
王小仙猛地站起,脸色铁青。片刻后,他沉声下令:“封锁消息,厚恤死者家属,严禁工匠议论事故原因。另派张九章即刻赶赴兰州,查明是材料缺陷还是操作失误。记住,告诉所有人??这不是失败,是通往安全之路必须付出的代价。”
待宋玉离去,他独自伫立窗前,久久不语。良久,取笔在《火器图谱》扉页添写一行小字:“变法之路,步步染血。吾愿以身为薪,燃尽黑暗,换一刻光明。”
次日清晨,他照常上朝,面带微笑,仿佛昨夜从未有过惊变。只有贴身侍从发现,那件紫绶官袍的袖口,隐隐透出几点暗红血渍??原来他在灯下反复修改火炮设计图时,不慎割破手指,却未察觉。
春风再度吹过黄沙边缘的定难城时,已是第二年三月。新一批硝石从西域运抵,火器研究院重建完成。而在这片曾经荒芜的土地上,一座座学堂拔地而起,琅琅书声取代了战鼓号角。孩童们不知“震天炮”为何物,却能背诵王小仙亲编的《惠民谣》:“糖不断,灯常亮;王公来,贼寇降。家中有粮心不慌,天下太平读文章。”
而在遥远的北方,辽南京的废墟深处,一只乌鸦啄开土层,叼起一片烧焦的纸屑。上面残留的墨迹依稀可辨:“东风已至……变法者不死,乾坤终将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