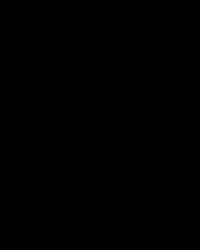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小户女 > 8090(第19页)
8090(第19页)
这周庄头走不动路,宝珠留下的那两个佃户一左一右将人架了起来。
“去将庄子里这些年收
租的册子拿出来我瞧瞧。”
周庄头只觉得腿软,走也走不动路,宝珠也不等他,开始问那两个佃户。
“如今你们每年交租是如何交的?”
周庄头眼似刀威胁地看了那两个佃户一眼,似乎晓得今天能做主的来了,这两个佃户心一横闭眼道,“每年收六成租子。”
听得收六成租,裴砚清眼皮跳了跳,“从前爹娘在时一年不过收四成租,你竟欺上瞒下——”
“他们…他们是胡说的!哥儿——万不可听这些刁人胡沁!”周庄头连滚带爬伏到裴砚清脚面上,“哥儿信我——”
宝珠已是不耐烦了,方才那些赌牌的也是战战兢兢,宝珠又问那佃户,“今年这一亩地产了多少粮?”
这佃户一一答了,宝珠算过更是心惊,便是今年田旱,一亩地少说也叫这周庄头昧下七八十斤粮食,当真是一肚子好算计。
裴砚清心下也觉得有愧,因他不管这一桩事儿,倒使得这些佃户日子过成这般,那吴管事管着铺面不过贪墨些银钱,这周庄头做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儿,若是天灾,这些佃户岂不是还要闹出人命来。
见这周庄头要倒霉了,其余人生怕牵扯到自己,一个接一个开始揭发这周庄头做下的恶事。
似乎晓得这儿有热闹看,庄子上几个没赌钱的也一起出来了,晓得是主家来了,争相来告这周庄头的状。
周庄头不光克扣佃户,还放印子钱给人收利钱。
宝珠叫人去他屋里将庄上的账册都找出来,被点到的人大气儿都不敢喘一下,只依着吩咐去拿账册。
账册有整整一箱,乱七八糟都堆在一起,今年的账册还没做,只找到一本收租的册子,各家交的租子都有账可查。
周庄头原还想狡辩,看今年收租账册被宝珠精准无误的翻出来,一句话堵在喉咙里说不出来,再看裴砚清已叫人取绳子来捆他,周管事软倒在桌边晓得躲不过,由人给他像死猪一样捆了个结实。
寻常与他关系好的,翻着眼儿两股颤颤恨不得马上昏过去,不单这周管事,方才那嘴里骂骂咧咧不干不净的几个也一并捆了起来。
“上回周庄头送田庄出息到汴京,想着今年大旱,庄户人家生活不易,此番来正好租子降一降。”宝珠一声冷笑,“却不想竟看到你们日子过得好似神仙。”
那一桌子鸡鸭鱼肉应当是昨儿晚上吃剩的,天冷汤汁也凝起来了,一桌菜只动了几口。裴家每月发下去的月钱够这周庄头过上好日子了,没想到还要吸这些佃户的血来满足私欲。
裴砚清晓得这官场腐败,却不想底下人贪腐起来也不遑多让,看过账目,粗略一算都十分骇人。
宝珠冷着一张脸坐着将账本来回翻了几遍,到末了连话也不愿再说,只叫裴砚清先将人关起来,“一天喂一餐稀粥吊着命,年后直接送去衙门里。”
那留下的两个佃户对视一眼,如同看到了救命稻草一般。
一早才来,宝珠将账算过,往年这些佃户们多出的租子都需得还回去,周庄头怕死,将自个儿银钱藏在哪儿抖落了个干净,即便他不说,裴砚清也能寻到藏钱的地方。
到天黑各家账目还没算清,明儿就是大年三十了,她也没有多余的功夫耗在这儿,开春后田地要育种,不能耽搁功夫,那两个佃户仍候着等她给准话,宝珠收了手里正写的账。
盘了大半日,这庄子里银钱怎么算也对不上,宝珠算着每年收来的租子与出息各是多少,裴砚清则在一边算着要退与人家的钱粮。
也实在不能耽搁,便将这些佃户明年要租的田地先算清楚,另外从前每年叫周庄头克扣下的钱粮也需得还给这些佃户,往年的账难理,宝珠只能将去年前年还有今年租子的算出来,好给佃户们先退一部分。
“你回去与大家伙儿说清楚,往后年成好,一年照旧是四成租,像今年闹了旱,明年租子便给大家少一成。”宝珠看了一眼屋里剩下的人,又继续说道,“明年几个庄子要换个庄头,裴家惯来只收四成租,往年这周庄头从中多扣下的钱粮,这几日先与你们退一些,等算清了都照旧还给你们。”
这两个佃户将宝珠的话一一记下,晓得明年只收三成租,对视一眼满脸不可置信。将这周庄头克扣下的钱粮一算,等到时候这些钱粮退了,管明年交租还有的多。
这二人似乎觉得天上掉了个大馅儿饼,被砸的晕晕乎乎,出门相互掐了一顿这才晓得不是做梦,欢欢喜喜挨家挨户将这消息说了一通,这消息一砸过来,个个晚上都没睡着,只盼着天亮好去问清楚是不是真的,还是这两人路上叫什么东西魇着了回来说的梦话。
今儿账没算完,明儿还是得再过来一趟。只一早在老宅子里头吃了早食,到现在天都黑了还没吃上一口饭,回去路上宝珠方才觉得肚饿,裴砚清自到了看到那些佃户便开始少言寡语起来,宝珠晓得他心里愧意甚浓,便说,
“横竖咱们来这儿是办事的,今年也不过年了,这几日先紧着将账算出来,给那些佃农发下去,这好叫他们过个好年。”
裴砚清在车架上瓮声瓮气应声,一只手伸进车里,感受到握上来的暖意,轻轻与她道了声谢。
第二日一到,昨日那些佃户全在门口候着了,不过今儿没昨儿那样愁眉苦脸,个个手里提着些自家寻常舍不得吃的咸肉腊肠一类,宝珠哪里好收,只叫他们先回去,又与他们说年后便换个庄头管事。
裴砚清一夜没睡,将这两年应当退与人家的银钱算清了,今儿正好全退与这些佃户。
庄子里头定要换个管事的,且这事儿还需得是个熟手,否则定要乱套。
周庄头叫捆起来了,其余人自然不会这般轻而易举揭过,素日与那周庄头交好帮着做下恶事的,都一并捆了,一来二去庄子里头只余七个人,其中一个素来与周庄头不对付,上回周庄头私下做的那些事儿,都是他检举的,叫欺压这些年,恨不得添油加醋将周庄头做下的恶事写成书叫宝珠评判个公道。
他只当自个儿告发了周庄头,自个儿便能提拔成管事的,私下已与相熟的摆了几桌酒恨不得立时就庆贺起来了,奈何宝珠心中有数,且不说这些年他一句话不提,就是上回门口那些佃户敲门他分明带着人在后院听得清楚,却压根不做理会,若有朝一日得了势,与那周庄头也没什么分别。
宝珠思来想去倒真有个合适的人选。
蒋实在许州已经能担的起来事儿了,只是若叫他来平阳县,恐还是管不住这一大摊子,倒是石地主早年走南闯北,人要老成些,从前他那些田地由他一人打理的井井有条,最主要的是,他是个很爱护田地的人。这一趟回去她是打算叫石地主来接手这头,签个三年五年的契,若是他肯,签长些也可以,工钱开高些,也不知他愿不愿意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