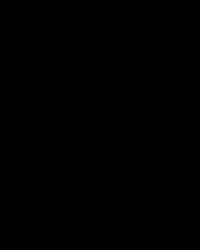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恋谣 > 第4章 中学(第3页)
第4章 中学(第3页)
尽管在早读课前十分钟冲进了教室,我还是被作为开学伊始就“踩点”的典型,在讲台上挨了一通不轻不重的训斥。
倒数第二排靠窗的位置成了我的避风港。
这里光线充足,又能将教室大半景象尽收眼底,还足够隐蔽,不易被老师频繁关注。
我喜欢这里,仿佛能在这里喘口气,暂时卸下“哥哥”和“新生”的双重负担。
第一节数学课,内容简单得令人发指,不到半节课,我已了然于胸。
剩余的时间,便成了漫长而枯燥的折磨。
老师的讲解声变成了嗡嗡的背景音,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飘向窗外。
思绪飘向了另一个人。
我的妹妹……她的成长速度似乎超出了我的预估。
那份沉静和偶尔流露出的洞察力,已不太像个懵懂的小学生。
她对铅字中毒症状已经更甚于我。
我毫不怀疑,若没有我监督,她能天天抱着书熬到深夜,然后早早给自己架上近视眼镜——等等,她戴上眼镜会不会更好看?
这个念头让我怔了一下,竟有些想象不出。
甩开这种无关紧要的想法,我担心起妹妹能否适应各种变化。
自从奶奶在家跌倒昏迷,父母连夜赶回老家,留下我和小遥在空荡的房子开始,生活的天平就彻底倾斜了。
母亲绝大部分时间都耗在了医院的病床前。
父亲则像一头沉默的、被生活压弯了脊梁的老黄牛,面对不断累积的医药账单,常常工作到深夜才拖着疲惫的身躯归来。
最初,妈妈还试图在白天提前做好晚饭,让我们只需微波炉加热。
然而我“作死”的证明自己能够独立做出可以入口的饭菜,于是爸妈理所当然地将“掌勺”重任移交给了我,好在每周的生活费从不短缺。
洗衣、扫除……这些琐碎的家务也自然而然地落在我肩上,连同照顾小遥的一切——换衣、梳头、检查作业、提醒作息……不知不觉间,我已成了她半个家长。
“顾业铭!”一声尖锐的呵斥伴随着一小截粉笔头精准地砸在我的课桌上,打断了我的神游。“上来!把这道题的解法写给大家看看!”
所幸题目不难。
我走上讲台,在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流畅地写下步骤。
老师挑剔的目光扫过板书,没找出什么错处,只不咸不淡地抛下几句“上课要专心”“不要以为进了重点就高枕无忧”之类的说教。
回到座位,我索性将那些沉重思绪暂时抛诸脑后,转而思考起当下和未来。
失去了与妹妹形影不离的校园时光,那片空出来的时间,或许正是打开新世界大门的钥匙?
也许,我该学着像其他正常的初中生那样,尝试拓宽自己的社交圈,去触碰那些名为“青春”的、躁动而模糊的边界?
课间的铃声像是解开了某种束缚。
教室里瞬间沸腾起来。
同学们像找到了各自磁极的铁屑,迅速聚集成一个个小团体,兴奋的交谈声、嬉笑声此起彼伏。
我坐在窗边,像个局外人。
环顾四周,无人向我投来目光——意料之中,甚至谈不上什么失落。
“无非是多看两本书打发时间罢了”。我继续阅读手中被翻得有些卷边的《曼弗雷德》,将自己沉入拜伦构筑的、充满痛苦与禁忌的精神世界。
这本书我读过太多遍,曼弗雷德与他容貌酷似的妹妹安丝塔帝之间那悖伦的、导致后者死亡的恋爱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永恒的精神折磨,种种情节我早已烂熟于心。
曼弗雷德最终的渴望是彻底的遗忘——遗忘自我,遗忘一切痛苦的根源。
第一次合上书页时,我就笃定:这本书绝不能给小遥看——至少不能由我亲手递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