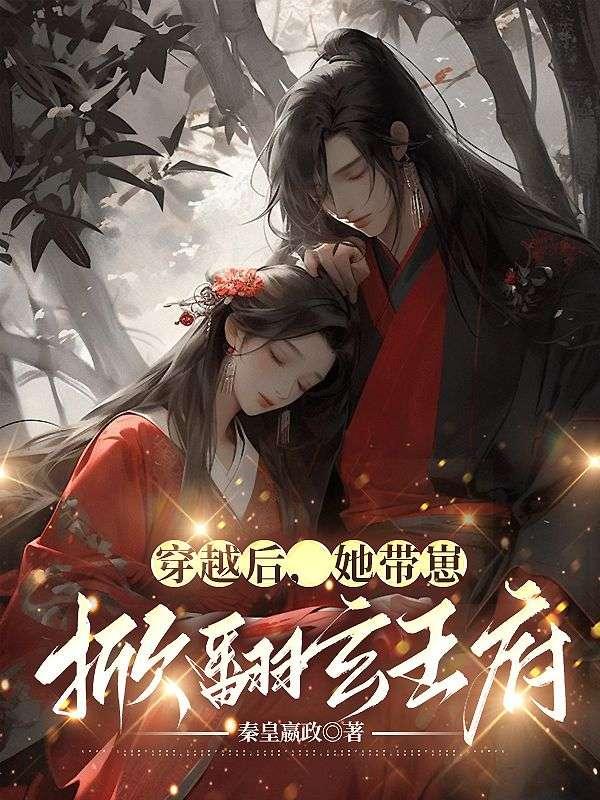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朱元璋的官,狗都不当 > 第一百八十三章 北上前的准备(第2页)
第一百八十三章 北上前的准备(第2页)
一个月后,春祭大典在即。按照祖制,诸王须齐聚太庙,共襄盛典。李可亲自督查安保部署,调换守卫班次,严禁任何亲王带兵入城。又下令关闭京城九门,实行宵禁三日。
祭祀当夜,月黑风高。忽有锦衣卫飞马来报:西直门外发现一支伪装成商队的武装队伍,共计三百余人,携弩机、火药,旗帜藏于车内,疑似欲趁乱攻城。
李可立即下令围捕,当场擒获为首者??竟是燕王府长史。搜出密信一封,上书:“事成之日,立少主,清君侧,废伪政。”
证据呈至御前,建文帝双手颤抖,泪流满面:“皇叔竟真要造反……”
李可跪地叩首:“陛下,此刻不是悲伤之时,是决断之刻。请即下诏:削燕王爵位,查抄王府,其余诸王若敢包庇,一体问罪。同时,宣读《官鉴录》第七案??景川侯谋逆始末,让百官明白,叛国者终将粉身碎骨。”
圣旨下达,雷霆万钧。燕王府被查封,党羽被捕数十人,供词牵连兵部、工部数名官员。一场风暴席卷朝野。
事后,建文帝问李可:“老师不怕此举激化矛盾,引发更大战乱?”
李可答:“怕。但我更怕沉默纵容,养虎为患。今日不动手,明日就是刀兵相见。与其等他羽翼丰满举旗反叛,不如在他刚露獠牙时打断脊梁。况且??”他望向宫外,“百姓已不再沉默。他们愿意相信朝廷,愿意配合调查,愿意站出来指认贪官。这就是新政最大的胜利。”
岁月流转,新政推行至第十二年。
全国设立巡按御史团三十六支,轮换巡察,无固定驻地;政务公开榜覆盖每一州县,百姓举报奖励提升至十两白银;连坐追责制度不断完善,主官责任细化至财政、司法、治安三大领域,失察即惩,瞒报加重。
科举改革深化,增设“实务科”,考算学、律法、水利、农政,录取者优先派往边远地区任职。女子参事班扩招,已有十七人进入户部、刑部实习,参与文书审核与政策拟定。
最令人振奋的是,民间自发兴起“清官榜”评选活动,由各地乡绅、塾师、商贾联合推举廉洁能干的地方官,张榜公示,竟成风尚。榜首之人,往往尚未接到朝廷嘉奖,已被百姓尊称为“青天”。
这一年中秋,李可独坐庭院,赏月品茶。婢女送来一封信,无署名,纸张粗糙,字迹歪斜:
“大人:
俺是山西赵家村的牛三娃,十年前您路过俺村,见俺娘饿得快死,让人送去半袋米。后来您走了,县太爷也换了,新官清查账目,把贪粮的粮长抓了,还退了我家三年租子。俺娘活到去年才走,临死前说,这辈子只见过您一个好官。
现在村里办了讲学堂,孩子们学写字、算数。俺儿子昨天回来,说考上了‘实务科’,要去河南当小吏。他问我,爹,做官能不能像李大人那样?
我说能。
因为您让我们相信,好人能赢。
??一个不识字的老农口述”
李可读罢,久久不能言语,泪水滑落杯中。
翌日,他在太子太傅府召集全体属官,命人取来一口大缸,盛满清水。
“诸位可知此为何意?”他问。
无人应答。
他缓缓取出一本《官鉴录》,投入水中。纸页遇水即散,墨迹晕染,字字模糊。
“这是提醒我们,制度若无人坚守,终将溶解于私欲浊流之中。今日我们尚能执法如山,明日也可能被人唾弃。所以,不要指望历史记住我们,只要求自己永不背叛初心。”
他顿了顿,声音低沉而有力:
“我老了,头发全白,腿脚也不灵便。但只要我还活着一天,就绝不允许任何人踩着百姓的头颅往上爬。哪怕他是亲王、是宰相、是天子身边红人,只要伸手贪赃、欺压良善,我就算拄拐杖也要站出来骂他一句??狗都不当的官,你也配当?”
全场肃立,无人言语,唯有心跳如鼓。
黄昏时分,李可独自步行至应天府衙门前。那里依旧挂着政务公开榜,今日更新的内容涉及河道治理经费分配。几位老农围着榜文,一边听差役诵读,一边争论某段堤坝是否真需花那么多钱。
李可站在人群后,默默听着,嘴角浮现笑意。
忽然,一名孩童转头看他,好奇问道:“老爷爷,你是做什么的?”
李可蹲下身,温和地说:“我啊,是个不愿再看着百姓流泪的普通人。”
孩子眨眨眼:“那你流泪过吗?”
李可怔住,片刻后轻轻点头:“流过。很多次。但只要你们将来不做坏官,我的泪就没白流。”
晚风拂过,吹动榜纸哗啦作响,如同千万人齐声应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