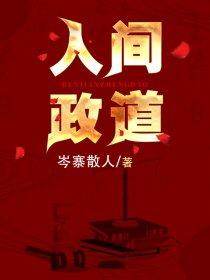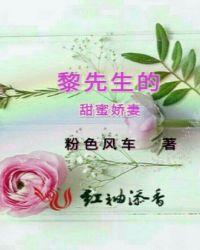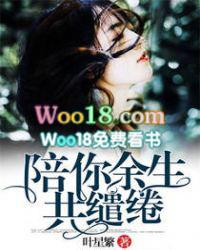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诸天影视从四合院开始 > 第九十七章 附加值带来的便利(第2页)
第九十七章 附加值带来的便利(第2页)
田晓霞也微微点头致意,一阵微风吹过,拂动了她前的短发。
“二位记者同志,辛苦了!”
李建国紧紧握着叶晨的手,语气显得十分诚恳,目光却不易察觉地快速扫过两人略显风尘仆仆的衣着和叶晨肩上那个半旧的采访包,然后说道:
“感谢你们深入一线,挖掘并报道了王世才同志这样的英雄典型!你们的报道,不仅弘扬了社会正气,也对我们铜城市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监督和推动作用啊!”
他说话时,旁边锅炉房恰好传来一声沉闷的排气声,仿佛在为他的话语加注标点。
这番话说的冠冕堂皇,滴水不漏。然而,在他心底深处,对这两位不速之客并非没有怨气。
他们像两股悄无声息却又精准无比的穿堂风,完全绕开了地方和矿上精心构筑的“门户”,打了个彻头彻尾的措手不及,让他和整个市委市政府都陷入了极大的被动,这无异于在他脸上扇了一巴掌。
这种不按常理出牌的方式,让习惯了掌控局面的李建国感到非常不适。
但是,李建国能坐到这个位置,绝非莽撞之人。在上午看到报道,尤其是注意到“本报记者叶晨田晓霞”的署名时,他就留了心。叶晨这个名字,对他这个文学爱好者来说,实在太耳熟了。
陕省文坛近几年风头最劲的青年作家,作品屡获好评,读者众多。他甚至隐约听到过一些小道消息,说作协的“黑老”从主席位置退下来时,属意的接班人就是这位叶晨,只因他年纪实在太轻,资历尚浅,才未能如愿。
要知道,国内最年轻的作协主席铁凝,担任省级作协副主席时也已接近三十,成为正职主席时三十九岁,这已经是破格的记录了。叶晨才二十多岁,其潜力可见一斑。
为了确认此叶晨是否彼叶晨,李建国还特意通过关系向省作协内部打探了一下。反馈回来的消息证实了他的猜测:这位叶作家大学毕业后确实进入了省报新闻部,据说实习时还是“黑老”亲自关照的。
这层文化界的背景和潜在的人脉,让李建国不得不高看一眼。他脑海中甚至浮现出叶晨某本书的封面,那深沉厚重的风格,与眼前这个目光沉静,举止从容的年轻人隐隐重合。
而更让他心惊的是叶晨身边那个看起来清秀干练的女记者??田晓霞。他打听之下,得知她的父亲竟然是田福军!
黄原地区的一把手,兼省委副书记,是省里排名前三的重量级人物!这个身份,如同一声惊雷,足以让李建国将所有的不满和怨气牢牢压在心底,并且必须表现出十足的善意和尊重。
他眼角的余光瞥见田晓霞那双清澈而带着审视意味的眼睛,心里不禁又掂量了几分。
作为同城主管工业的领导,李建国深知人脉和背景的重要性。得罪一个背景深厚的省报记者,尤其是其背后还站着田福军这样的人物,绝对是极不明智的。与其结怨,不如趁机结交。
远处,煤矿提升井架的巨大轮子在蓝天背景下缓缓转动,发出有规律的轰鸣,仿佛在提醒着这里的一切都围绕着权力和资源的轴心运转。
“叶记者的大作,我可是拜读过不少啊!”
李建国笑容可掬,开始拉近关系,试图将这场路边寒暄营造得更像一次文人雅士的偶遇,只见他继续说道:
“没想到您不仅在文学上造诣深厚,新闻工作也做得如此出色,真是文武全才!”
李建国手势幅度不大,却带着一种试图掌控谈话节奏的惯性。他又转向田晓霞,语气更加和蔼,甚至带着一点长辈的关切:
“田记者也是年轻有为,笔锋犀利,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二位这次可真是给我们铜城‘送’来了一面镜子,照出了我们工作中的不足啊!”
他的话语里,既有对两人能力的恭维,也隐晦地表达了“不打招呼”带来的困扰,但姿态放得很低,完全是协商和沟通的语气。一阵卷着细碎煤尘的风吹过,他下意识地侧了侧身,用手在面前轻轻扇了扇。
叶晨何等聪明,自然听出了李建国的弦外之音,也明白他态度如此客气的原因。
他微微一笑,既不居功,也不怯场,回应得体的同时,也保持着记者应有的独立立场:
“李市长过奖了。我们只是做了记者该做的事情,如实报道真相。王师傅的事迹感人至深,我们也不忍英雄被埋没。
相信在市里的重视下,后续的善后和宣传工作一定能做得更好,这也是对王师傅在天之灵最好的告慰。”
叶晨的声音平和,却像井下的掘进机一样,稳稳地向前,不着痕迹地重申了媒体的监督职责。
一番看似平和,实则暗含机锋的寒暄在弥漫着工业气息的院门外进行着。阳光透过薄薄的煤尘,给三人的身影镀上了一层有些朦胧的光晕。
李建国的主动示好,既是迫于形势,也是基于对两人背后能量的权衡。而叶晨和田晓霞,则凭借着职业的敏锐和潜在的背景,在这矿区特有的背景音中,在这场无形的交锋中,稳稳地站在了有利的位置。。。。。。。
结束了铜城之行,叶晨和田晓霞坐上了回省城的飞机。飞机引擎的轰鸣取代了矿区的嘈杂,舷窗外是绵延的云海和下方逐渐缩小的黄土沟壑。
田晓霞靠在座椅上,回想起李建国那张热情周到,却又让人感觉隔着一层的脸,忍不住撇撇嘴,对身旁的叶晨吐槽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