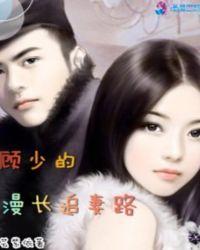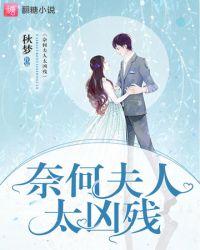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徒弟,不要丢下为师去当勇者啊! > 第167章 父女(第2页)
第167章 父女(第2页)
人群静静伫立,无人喧哗。他们不是来求答案的,也不是来听教诲的。他们是来传递的??把那一碗面的温度,把那一盏灯的光亮,把那一句“我愿承其志”的誓言,亲手交到下一个手中。
小梨走进屋内,取出一本崭新的《心灯录》,翻开第一页,在空白处写下四个字:
**“由你开始。”**
她将书递给阿禾。
少女双手接过,深深鞠躬。
随后,人们依次上前,取走一本抄本,或留下一盏灯,或献上一碗面。没有仪式,没有口号,只有沉默中的郑重,平凡里的庄严。
当最后一人离去,小梨站在门口,望着远去的背影,忽然觉得前所未有的轻松。
她知道,这场战争从未真正结束,也不会彻底终结。影阁的意志或许会以新的面目重生??也许是某个宣称“唯有我能拯救世人”的狂人,也许是一个打着“秩序”旗号剥夺自由的政权,甚至可能是人心深处日渐滋长的麻木与冷漠。
但她也知道,只要还有人愿意为陌生人递上一碗面,只要还有人在黑暗中点亮一盏灯,只要还有少年读完《心灯录》后抬起头说“我也能做到”,那么心灯就不会熄灭。
几天后,小梨离开了桃林。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有人说她隐居深山,著书立说;有人说她游历四方,传道授业;还有人说她在某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独自登上极北冰原,将锈剑埋入虚妄之门的废墟之下,然后席地而坐,守了一夜。
但确凿的是,一年后的春日,桃林中最老的那棵桃树下,出现了一块新碑。碑上无名,只刻着一行小字:
**“他曾教我吃饭不要撒汤。”**
孩子们常来这里玩耍,摘花、荡秋千、讲故事。每当有人问起这块碑是谁立的,村里的老人就会笑着指向厨房里正在煮面的那个年轻女子??正是阿禾。
她如今住在桃林边的小屋里,每天清晨为过往行人煮一碗面,分文不取。若是有人问她为何如此,她便笑着说:“因为我吃过那样的面。”
而在千里之外的南方港口,一艘商船正准备启航。甲板上站着一名青年水手,肤色黝黑,目光坚毅。他腰间别着一枚玉佩,样式古朴,边缘已有磨损。临行前,他从包袱里取出一本破旧的《心灯录》,翻到最后一页,提笔添上一句:
**“若有一天你感到害怕,请记住:你曾点亮过光。”**
他合上书,望向远方海平线。朝阳升起,万丈金光洒在波涛之上,宛如一条通往未知的光明之路。
同一时刻,西陲荒漠中的绿洲村落里,一位盲眼老妪正坐在门前纺纱。她的孙女靠在她膝头,听她讲述一个关于“锈剑老人”的故事。讲到一半,老妪忽然停了下来,抬头望天。
“奶奶,怎么了?”女孩问。
老妪微笑:“风里有面香。”
女孩皱眉:“可咱们还没做饭呢。”
老妪轻轻抚摸孙女的头:“那是心灯的味道。”
而在王城最贫民的巷子里,一个瘦弱的少年蜷缩在墙角,怀里紧紧抱着一本被人丢弃的《心灯录》残页。他饿得发抖,却仍用冻僵的手指一笔一划描摹着书上的字迹。忽然,一只粗糙的手递来一碗热面。
他抬头,看见是个满脸胡茬的乞丐。
“吃吧,”乞丐说,“活着才能继续写。”
少年接过面,眼泪砸进汤里。
他不知道,这个乞丐曾在二十年前是一名影阁执律使,奉命追杀林昭。但在某个雨夜,他亲眼看见林昭为一名垂死的敌军士兵盖上外袍,说:“他也想回家。”那一刻,他的心灯亮了。从此脱逃组织,流落街头,却始终记得那个背影。
此刻,他看着少年狼吞虎咽,嘴角微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