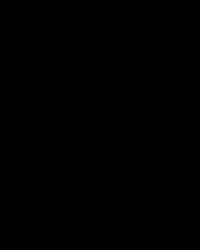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消渴 > 5060(第17页)
5060(第17页)
“话说得对才说。”
季秋的夜气温下降,陈运能够看到她耳下的皮肤绒毛在安静中纷纷起立:
“我并不在乎被你知道。”
“所以不用躲我,陈运。”
也不用再躲我的同时跑来跑去地给我送饭,使劲儿干所有事。
更不用吃药吃得那么乖。
药的副作用很大,你该下班后好好休息的……
陈运突然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她,左右张望一通,干脆转身去够搭在床尾的外套:
“我也没有太躲你其实。”
薄外套披上迟柏意肩膀,遮住了那点儿暖雪融光,陈运坐在她腿上直起腰,给她一颗一颗扣着外套纽扣:
“我就是心里有点不得劲儿。”
“你说你多好一个人啊,你非得看上我、我非得看上你。结果搞得你怪不好受的——抬下巴,头发钻扣眼儿里去了。”
迟柏意本想说个什么,没说出来,只好先乖乖抬下巴,任由她动作。
“而且我那天晚上也真没觉得尴尬或者别的什么……”陈运说到这儿时愣了愣,又接着往下说,“不然这几天也不会跟你一起睡床了。我就是心疼你。”
至于躲?
“我没有。”
这一番话真心实意,坦荡得能叫人一眼看透那颗心。
迟柏意一时回不过神,回过神来后只觉心中酸软,想照着平时再开两句玩笑活跃一下气氛,或者原样煽情回去,又觉得说什么都不如那一句“我心疼你”。
陈运眼睛好亮好亮,眼底清透得像玻璃。
床头的窗户没有关紧,风吹进来,窗帘一下一下扬起,那双眸子就在帘子后,若雾屏云幔,朦胧模糊。
这一刻,洗手间的水滴声落得很急。
迟柏意抓住窗帘一角,另一只手捂住了她的眼睛——
她的动作仓促而突然,放在从前陈运会下意识拍开退后。
可这一回,陈运动都没动一下,就由着那只手覆上去,看着眼前一片漆黑:
“迟柏意?”
睫毛如蝶翼扑棱在掌心,三五下后刮得皮肤滚烫。
迟柏意应着:
“嗯。”
“我都知道的。”
迟柏意依旧只是说:
“好。”
“我会好好吃药,会变好,会很快的。什么都会好,我们也总会好好的。你……”
你等等我。
迟柏意手一松,帘子无声垂落,风停,水止。
窗旁,她睁眼:
“不过也不妨碍我心疼你,所以你就让我疼疼呗。”
“那你这两天跑哪儿去了?”迟柏意总算想起自己要问什么,伸手点点她鼻子,“别打岔,也不许这么招我心软——当我没发现?白天下了班也不回家。”
陈运从善如流地翻脸,支支吾吾地敷衍:
“嗯也没有,就外头随便走走,不是周大夫说叫呼吸新鲜空气什么的。”
她不说,迟柏意也不再追着问,坐起来叫她起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