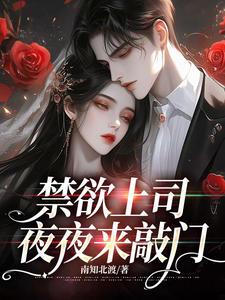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我一个三金导演十项全能很合理吧 > 266我们与恶魔从来都不是朋友想试镜先考证求月票(第1页)
266我们与恶魔从来都不是朋友想试镜先考证求月票(第1页)
“睿哥,来啦。”
“吕导早上好。”
“……”
吕睿刚踏入《南京照相馆》的试镜区,此起彼伏的招呼声就涌了过来。
现场可谓是人来人往。
睿视界的员工正在整理资料,外来的演员则。。。
雪在凌晨四点停了。吕春站在片场外的空地上,呼吸凝成白雾,像一帧未剪进电影的慢镜头。他刚从梦中醒来,那片发光的冰原还在视网膜上残留着余影,仿佛整部《潮汐》不是由他拍摄,而是从大地深处自行生长出来的。手机屏幕亮起,是“星火协议”系统自动推送的警报:全球已有六万两千三百一十七个节点完成接入,其中百分之七十三来自中国境内,其余遍布东南亚、欧洲、北美和非洲华人社区。
“它活了。”吕春低声说。
他没有回屋,而是走向摄影棚最深处那个被封存的角落??那里停着一台老式胶片放映机,是侯宏亮托人从内蒙古一个废弃文化宫里找回来的,机身锈迹斑斑,齿轮却还能转动。吕春亲手接通电源,将一段未经公开的《北境》原始素材塞入片槽。银幕亮起的瞬间,画面竟不是刘艺菲站在雪地举摄像机的那一幕,而是一段从未录入正式版本的街头实录:2003年冬,哈尔滨中央大街,一个穿军大衣的男人蹲在路灯下,用冻裂的手指翻看一本泛黄的日记本。镜头晃动得厉害,显然是偷拍。男人抬起头,露出半张脸??正是年轻时的林骁。
吕春屏住呼吸。
这段影像他从未见过。标签上写着:“2003。12。17,林骁返乡途中,自述‘我签了那份名单,但我没烧书’。”
他猛地合上机器,心跳如鼓。这不是档案馆遗漏的资料,也不是“光库”收录的内容,它是某种更隐秘的东西??记忆的反噬。那些你以为被压下去的声音,终会在某个雪夜重新浮现。
清晨六点,团队陆续抵达。林晚第一个冲进来,手里攥着打印纸:“你看了吗?青海数据中心昨晚遭到三次网络攻击,IP都伪装成国内用户,但‘星火协议’的追踪模块捕捉到了加密特征,和公安部之前锁定的那个境外NGO一致。”
“他们想吓我们。”吕春坐到剪辑台前,打开最终版《静水》的工程文件,“可他们不知道,真正的数据已经不在服务器里了。”
小陈递来热粥,欲言又止:“网上……开始有人说你是‘记忆狂魔’,说你在煽动对立,制造创伤依赖。”
吕春笑了笑:“让他们说。等《涨潮》上映,他们会发现,我不是在制造记忆,我只是把锁在抽屉里的钥匙交还给主人。”
当天下午,《静水》进入最后混音阶段。配乐师老周戴着耳机,反复调试一段长达八分钟的无声段落??那是影片中一位老人在废墟里翻找旧照片的全过程,没有任何背景音乐,只有风声、纸张摩擦声、偶尔一声叹息。国外合作方提出加一段悲情弦乐,被吕春否决。
“这不是给他们听的。”他说,“这是给经历过的人听的。他们不需要音乐告诉我什么叫悲伤。”
傍晚收工时,刘艺菲打来视频电话。她正在云南某山村参与“口述史救援队”的采录工作,身后是一间低矮的土屋,墙上挂着褪色的全家福。“今天这位奶奶讲了整整五个小时。”她声音疲惫却发亮,“她说她丈夫是知青,六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后来死在劳改农场。她一直不敢说,怕连累孩子。可昨天她孙女带她看了《北境》,她突然哭了,说‘原来有人记得’。”
吕春望着窗外渐暗的天色,轻声问:“然后呢?”
“然后她拿出一个铁盒,里面全是信,几十年没寄出去的情书。”刘艺菲顿了顿,“我把它们录了下来,上传到了‘光库’。编号是YNN-0439。”
“替我谢谢她。”吕春闭上眼,“也替那些收不到回信的人。”
挂断后,他调出“光库”后台日志,输入编号。那段音频只有三十七秒,男人的声音年轻而温柔:“小梅,今天我种了一棵梨树,我说好了,等它开花那天,我就回来娶你。”背景有鸟叫,有锄地声,还有远处广播念语录的杂音。吕春把这段音轨导入《静水》第48分钟处,插在一位女儿整理母亲遗物的场景之后。没有字幕,没有提示,就像一段偶然飘来的风。
第二天,“星火协议”迎来第一次真实考验。
凌晨两点,哈尔滨电力系统突发故障,片场备用电源仅维持两小时。技术组紧急启动离线备份程序,却发现主服务器已被远程植入木马,试图批量删除与“林骁证据包”相关的元数据。千钧一发之际,“星火协议”的分布式验证机制自动激活,全球数千节点同步响应,重新拼合出完整信息流,并反向标记入侵源。
天亮时,公安部门通报:攻击来自一个伪装成学术机构的海外组织,其资金链可追溯至十年前打压《茧》系列展览的同一财团。
“他们还不死心。”制片人咬牙。
“那就让他们看清楚。”吕春站起身,走向录音室,“我要录一段新旁白。”
他戴上耳机,面对麦克风,声音平静如深水:
>“你们以为删掉记录就能抹去发生过的事。可你们忘了,记忆不是存在硬盘里的文件,它是母亲教孩子唱的第一首歌,是父亲藏在工具箱底层的老照片,是某个深夜,一个人突然想起早已去世的亲人说过的一句话。
>
>你们可以关掉一台服务器,但关不掉千万人心中的回放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