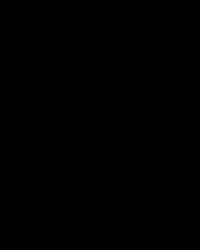顶点小说网>屠户家的娃娃亲夫郎 > 6570(第15页)
6570(第15页)
因心里已经多少有了个底,两人这会儿心里也没多慌乱了,反而多了几分高兴和期待。
到了福兴楼以后,那伙计直接将人引上了二楼一个雅间。
推开门,只见孙掌柜早已等在那儿了,桌上上了一桌的菜,有酱鸭、清蒸鱼、辣炒河虾等等,虽说都称的上是福兴楼的招牌菜,但也不至于过分夸张,除此之外还有一壶酒。
由此便能看得出,孙掌柜算是很有诚意的了。
一见两人来,孙掌柜便站了起来,也没摆架子,反而笑呵呵的迎了上来:“呦,这就是霍屠户和霍夫郎吧,快请坐。”
其实孙掌柜之前同霍青,江云苓都不认识,但孙掌柜每日在酒楼里迎来送往的,同人打交道早就习惯了,就是跟陌生人之间也能扯上几句,话也能说的叫人舒舒坦坦的,应付霍青和江云苓两个自然不在话下了。
对于霍青和江云苓,虽说都是乡下来的,但孙掌柜心里也没瞧不上人家。
他自己个儿也是从酒楼的小伙计一步一步干上来的,这么些年,什么人没伺候过,也没觉得拉不下脸,更何况他还想买人家的方子。
但要说十分热切,那也够不上,毕竟身份在那儿。
反正该客气的,该给的面子他给了,至于谈的怎么样,成不成,那得看后头了。
先礼后兵嘛,实在谈不拢了再敲打不迟。
对于孙掌柜的热情,江云苓有些不习惯,倒是霍青出来做生意几年,比江云苓好些。
“孙掌柜。”两人上前也客客气气的给孙掌柜点头问了句好。
伙计带着他们进了雅间以后便关上门出去了,孙掌柜热情的招呼着他们坐下,也没说什么事儿,只一味让先吃饭,别的事儿等吃饱了再聊。
一会儿又笑说:“哎呦,早想认识认识霍屠户和霍夫郎了,霍夫郎这吃食做的好哟,如今城里还有谁不知道这南乳哟,连咱们酒楼的食客来吃饭时都说呢。”
霍青和江云苓也不傻,见孙掌柜没提,两人便全当不知道这事儿,只安安心心吃饭,不时应和两句,霍青还时不时给江云苓夹口菜。
福兴楼可是这城里最大,最好的酒楼了。他们这些农户人家,平日里是极少会能到城里的酒楼来吃饭的。
光是这一桌子菜估摸着就要不下二三百文,一般人哪里舍得,既然孙掌柜的说是请他们来吃饭的,那就先安心把肚子吃饱了再说。
直到一顿饭吃饱,孙掌柜这才终于提起了正事儿。
只见孙掌柜笑了声,放下手里的酒杯,又把两人夸了一遍:“没想到霍兄弟是个这样直爽的人,连夫郎也如此贤惠。”
而后才提起的正事儿:“我也不瞒你们了,今日请两位来,其实是想和霍夫郎谈谈你最近在卖的那南乳的事儿。”
“明人不说暗话,我已经和老板商量过了,酒楼想出钱,买了霍夫郎手里的南乳的方子,不知霍夫郎可愿意?”
闻言,霍青挑了挑眉,将手里的碗筷放下。
果然是为着这个事儿来的。
同张记菜馆那样躲在暗处使阴招比,孙掌柜作为福兴酒楼的掌柜的,不管他心里怎么想,做出来的事儿至少是以礼相待,好酒好菜的招呼着,要做什么也是明着来,这已是给足了尊重了。
其实为这事儿,他们俩在家也商量过好几次了。
城里各大酒楼食肆都已经盯上他们家南乳生意了,同人家家大业大,后头还有靠山,他们这种乡下的泥腿子是比不过的,因而在这个当口,要是有机会把南乳的方子卖了那是再好不过的。
虽然以后便不能靠这个营生了,可他们每日卖肉才挣多少钱,卖个方子又能挣多少钱。
再说了,方子卖了,那酒楼能拿它怎么赚钱,赚多少钱,那都不是他们操心的事儿了,也不会再有人为了这事儿盯上他们家。
而这方子怎么才能保住,人家酒楼自然有他们的办法。
夫夫俩对视一眼,霍青眼里有些笑意,对江云苓点了点头。
南乳是江云苓辛苦做出来的吃食,也是夫郎一直在卖,方子卖不卖,自然也是他说的算。
于是,江云苓抿抿唇,笑了:“掌柜的如此痛快,那我也就明说了。福兴楼既想出钱买方子,我自然是愿意的。”
话落,只见他苦笑了一下,又道:“前些日子的事儿,只怕孙掌柜也听说了吧。”
这话一说,孙掌柜忙点头应和了一声:“欸,听说了听说了。嗐,说起来,霍夫郎这也是遭了无妄之灾了。”
其实这事儿城里大多数酒楼食肆都已经知道了,就是张记菜馆做的,想来霍青夫夫俩心里也清楚,不过此时江云苓既没有明说,孙掌柜自然也只能跟着含糊着带了过去。
与此同时,孙掌柜又看了眼霍青,见他没有开声的意思,心里多少有些惊讶。
虽说他也清楚这南乳的营生是这霍夫郎做的,只不过涉及到买卖方子这样的大事儿,一般都是由家里的汉子拿主意的,所以他还特地嘱咐了店里的伙计,请人的时候得把霍青也一并请来。
却没想到应话的人仍是江云苓。